第九卷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起显庆元年三月谢慈恩寺碑成终三年正月随车驾还西京。
显庆元年春三月癸亥御制大慈恩寺碑文讫。时礼部尚书许敬宗遣使送碑文与法师。鸿胪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师率寺众诣阙陈谢曰。沙门玄奘言。被鸿胪寺符。伏奉敕旨。亲纡圣笔。为大慈恩寺所制碑文已成。睿泽傍临宸词曲照。玄门益峻。梵侣增荣。局厚地而怀惭。负层穹而寡力。玄奘闻。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圣人之道。亦因辞以见情。然则画卦垂文。空谈于形器。设爻分象。未踰于寰域。羲皇之德。尚见称于前古。姬后之风。亦独高于后代。岂若开物成务。阐八正以摛章。诠道立言。证三明而导俗。理穷天地之表。情该日月之外。较其优劣。斯为盛矣。伏惟皇帝陛下。金轮在运。玉历乘时。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将圣。功茂乃神。纵多能于生知资率由于天至。始悲奁镜。即创招提。俄树胜幢。更敷文律。若乃。
天华颖发。睿藻波腾。吞笔海而孕龙宫。掩词林而包鹤树。内该八藏。外核六经。奥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给园遗迹。托。
宝思而弥高。奈苑余芬。假琼章而不昧。岂直抑扬梦境。照晢迷涂。谅以镕范四天牢笼三界者矣。玄奘言行无取。猥预缁徒。亟叨恩顾。每谓多幸。重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惭且跃。实用交怀。无任竦戴之诚。谨诣朝堂。奉表陈谢。乙丑。法师又惟。主上文明天纵。圣而多能。非直文丽魏君。亦乃书迈汉主。法师以见碑是圣文。其书亦望神笔因诣阙请皇帝自书。表曰。沙门玄奘等言。窃以应物垂象。神用溥该。随时设教圣功毕尽。是知日月双朗。始极经天之运卉木俱秀。方穷丽地之德。伏惟皇帝陛下。智周万物。仁沾三界。既隆景化。复阐玄风。鄙姬穆之好道。空赏瑶池之咏。蔑汉明之崇法。徒开白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远扬幽旨。用雕丰琬。长垂茂则。同六英之发音。若五纬之摛曜。敷至怀而感俗。弘大誓以匡时。岂独幽赞真如显扬玄赜者也。虽玉藻斯畅。翠版将刊。而银钩未书。丹字犹韫。然则夔乐已簨。匪里曲之堪预。龙乡既昼。何爝火之能明。非夫牙旷抚律。羲和总驭。焉得扬法鼓之大音。裨慧日之冲彩。敢缘斯义。冒用干祈。伏乞成兹具美。勒以神笔。庶淩云之妙。迈迹前王。垂露之奇。腾芬后圣。金声玉振。即悟群迷。凤翥龙蟠。将开众瞽。岂止克隆像教。怀生沾莫大之恩。实亦聿赞。
明时。宗社享无强之福。玄奘禀识愚浅。谬齿缁林。本惭窥涉。多亏律行。猥辱宸词。过蒙褒美。虽惊惕之甚措颜无地。而慊恳之勤。翘诚有日。重敢尘黩。更怀冰火。表奏不纳。景寅法师又请曰。昨一日蒙赍天藻喜戴不胜。未允神翰。翘丹尚拥。窃以攀荣奇树。必含笑而芬芳。跪宝玉岑。亦舒渥而贻彩。伏惟。
陛下。提衡执粹。垂拱大宁。睿思绮毫。俯凝多艺。鸿范光于涌洛。草圣茂于临池。玄奘肃荷前恩。奉若华于金镜。冒希后泽。伫桂影于银钩。岂直合璧相循。联辉是仰。亦恐非。
天翰。无以悬日月之文。唯丽则可以摅希微之轨。驰魂俯首。非所敢望。不胜积慊。昧死陈请。表奏帝方运神笔。法师既蒙帝许。不胜喜庆。表谢曰。沙门玄奘言。伏奉。
敕旨。许降宸笔。自勒御制大慈恩寺碑文。茧诰爰臻。纶慈猥集。只荷惭惕。罔知攸措。玄奘闻。强弩在彀。鼯鼠不足动其机。鸿钟匿音。纤莛无以发其响。不谓日临月照。遂回景于空门。雨润云[卄/丞]。乃照感于玄寺。是所愿也。岂所图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枢握符缵运。追轩迈顼孕夏吞殷。演众妙以陶时。总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内。既沐仁风。四天之表。亦沾玄化。然则津梁之法。非至圣无足阐其源。幽赞之工。非至人何以敷其迹。虽追远所极。自动天情。而冥祐可祈。即回宸眷英词曲被。已超希代之珍。秘迹行开。将踰绝价之宝。凡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庆跃。梦钧天之广乐。匹此非奇。得轮王之髻珠。俦兹岂贵。庶当刊以贞石。用树福庭。[蠢-日]彼迷生。方开耳目。盛乎法炬。传诸未来。使夫瞻宝字而仰银钩。发菩提于此日。讽遒文而探至赜。悟般若于斯地。劫城穷芥。昭昭之美恒存。迁海还桑。蔼蔼之风无朽。玄奘出自凡品。夙惭行业。既蒙落饰。思阐玄猷。往涉迦维。本凭。
皇化。迨兹翻译。复承朝奖。而贞观之际。滥沐洪慈。永徽以来。更叨殊遇。二主神笔。猥赐褒扬。两朝。
圣藻。极垂荣饰。顾循愚劣。实怀兢惧。输报之诚。不忘昏晓。但以恩深巨壑。岂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纤尘之可谢。唯当凭诸慧力。运以无方。资景祚于园寝。助隆基于七百。不任竦戴之至。谨附内给事臣王君德奉表。陈谢以闻。轻犯威严。伏深战栗。夏四月八日大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
敕。又遣大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幢最卑者。上出云霓。幡极短者。犹摩霄汉。凡三百余事。音声车百余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门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敕遣且停。仍迎法师入内。至十日天景晴丽敕遣依前陈设。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
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等于佛殿前。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师又与徒众诣朝堂。陈谢碑至寺。表曰。沙门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
敕旨。送御书大慈恩寺碑。并设九部乐供养。尧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辉。舜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广。丰碣岩[立*寺]。天文景烛。状彩霞之映灵山。疑缛宿之临仙峤。凡在缁素。电激云奔。瞻奉惊跃。得未曾有。窃以八卦垂文。六爻发系。观鸟制法。泣麟敷典圣人能事。毕见于兹。将以轨物垂范。随时立训。陶铸生灵。抑扬风烈。然则秦皇刻石。独昭美于封禅。魏后刊碑。徒纪功于大飨。犹称题目。高视百王。岂若亲纡睿藻。俯开仙翰。金奏发韶。银钩绚迹。探龙宫而架三玄。轶凤篆而穷八体。扬春波而骋思。滴秋露以标奇。弘一乘之妙理。赞六度之幽赜。化总三千之域。声腾百亿之外。奈苑微言。假天词而更显。竹林开士。托神笔而弥尊。因使梵志归心。截疑网而祗训。波旬革虑。偃邪山而徇道。岂止尘门之士。始悟迷方。滞梦之宾。行超苦际。像教东渐。年垂六百。弘阐之盛。未若于兹。至如汉明通感。尚咨谋于傅毅。吴主归宗。犹考疑于阚泽。自斯已降。无足称者。随缘化物。独推。
昭运。为善必应。克峻昌基。若金轮之王。神功不测。同宝冠之帝。休祚方永。玄奘等。谬忝。
朝恩。幸登玄肆。属慈云重布法鼓再扬。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门长辟。而顾非贞恳。虚蒙奖导。仰层旻而荷泽。俯浚谷以怀惭。无任竦戴之诚。谨诣。
阙陈谢以闻。碑至。有司于佛殿前东北角。别造碑屋安之。其舍复拱重栌。云楣绮栋。金花下照。宝铎上晖。仙掌露盘。一同灵塔。
大帝善楷隶草行。尤精飞白。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并穷神妙。观者日数千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模打。许之。自结绳息用文字代兴。二篆形殊。楷草势异。悬针垂露。云气偃波。铭石章程。八分行隶。古人互有短长。不能兼美。至如汉元称善史书。魏武工于草行。钟繇闲于三体。王仲妙于八分。刘邵张弘发誉于飞白。伯英子玉流名于草圣。唯中郎右军稍兼众美。亦不能尽也。故韦文休见二王书曰。二王自可称能。未是知书也。若其天锋秀拔。頵郁遒健。该古贤之众体。尽先哲之多能。为毫翰之阳春。文字之寡和者。信归之于我皇矣。法师少因听习。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岭。遂得冷病发。即封心屡经困苦。数年已来凭药防御得定。今夏五月因热追凉。遂动旧疾几将不济。道俗忧惧中书闻奏。
敕遣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针医上官琮专看。所须药皆令内送。北门使者日有数般。遣伺气候。递报消息。乃至眠寝处所。皆遣内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虽慈父之于一子。所不过也。孝璋等给侍医药昼夜不离。经五日方损。内外情安。法师既荷圣恩。翌日进表谢曰。沙门玄奘言。玄奘拙自营卫。冷疹增动。几至绵笃。殆辞昭运。天恩矜悯。降以良医。针药才加。即蒙瘳愈。驻颓龄于欲尽。反营魄于将消。重睹昌时。复遵明导。岂止膏盲永绝。腠理恒调而已。顾循庸菲。屡荷殊泽。施厚命轻。罔知输报。唯凭慧力。庶詶冥祉。玄奘犹自虚惙。未堪诣阙陈谢。无任悚戴之至谨遣弟子大乘光奉表以闻。
帝览表遣给事王君德。慰问法师曰。既新服药后气力固当虚劣。请法师善自摄卫。未宜即用心力。法师又蒙圣问。不胜喜惧之至。又表谢曰。沙门玄奘言。玄奘业累所婴。致招疾苦。呼吸之顷。几隔明时。忽蒙。
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忧。天使频临。有逾十慰。神药俯救。若遇一丸。饮沐圣慈。已祛沉痛。蒙荷医疗。遂得痊除。岂期已逝之魂。见招于上帝。将夭之寿。重禀于洪炉。退省庸微。何以当此。抚膺愧越。言不足宣。荷殊泽而讵胜。粉微躯而靡谢。方冀勖兹礼诵。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无穷之责。无任感戴之极。谨附表谢闻。喜惧兼并。罔知攸措。尘黩听览。伏增惶悚。往贞观十一年中有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时普光寺大德法常。总持寺大德普应等数百人。于朝堂陈诤。未蒙改正。法师还国来已频内奏。许有商量未果而。
文帝升遐。永徽六年有。
敕。道士僧等犯罪。情难知者。可同俗法推勘。边远官人不闲。
敕意。事无大小。动行枷杖。亏辱为甚。法师每忧之。因疾委顿。虑更不见天颜。乃附人陈前二事。于国非便。玄奘命垂旦夕。恐不获后言。谨附启闻。伏枕惶惧。
敕遣报云。所陈之事闻之。但佛道名位。
先朝处分事须平章。其同俗敕即遣停废。师宜安意强进汤药。至二十三日降敕曰。道教清虚。释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为法末人浇。多违制律。权依俗法。以申惩诫。冀在止恶劝善。非是以人轻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条。更别推科。恐为劳扰。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违犯宜依条制。法师既荷兹圣泽。奉表指阙。陈谢曰。沙门玄奘言。伏见敕旨。僧尼等有过停依俗法之条。还依旧格非分之泽。忽委缁徒。不訾之恩。复沾玄肆。晞阳沐道。实用光华。局地循躬。唯增震惕。窃以法王既没。像化空传。宗绍之规。寄诸明后。伏惟。
皇帝陛下。宝图御极。金轮乘正。眷兹释教。载怀宣阐。以为落饰玄门。外异流俗。虽情牵五浊。律行多亏。而体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条之密网。布以宽仁。信金口之直词。允兹回向。斯固天只载悦。应之以休征。岂止梵侣怀恩。加之以贞确。若有背兹宽贷。自贻伊咎。则违大师之严旨。亏圣主之深慈。凡在明灵。自宜谴谪。岂待平章之律。方科奸妄之罪。玄奘庸昧。猥厕法流。每忝。
鸿恩。以怀惭惕。重祗殊奖。弥复兢惶。但以近婴疾疹。不获随例指阙。无任悚戴之至。谨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陈谢以闻。自是僧徒得安禅诵矣。法师悲喜交集不觉泪沾矜袖。不胜捲局?痢S种亟?硇辉簧趁判?恃浴7?疃麟贰3??纫浪追ㄍ瓶碧跽隆O泊髦?摹D??计?G匝罢??√妗K婢?纤?盅铩R吐缀癖 Y承?缫孕巳薄W允ピ嗽阼?C骰手创狻U绯绲酪铡G?鹦?濉

粤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于大月氏王使者而震旦教始萌芽。其后,摄摩腾、竺法兰随汉明帝求经使臣蔡愔等至洛阳,而四十二章等经乃缄于兰台石室。魏晋而降大德迭与翻译通明中西不隔。达摩西来,演畅宗风不立文字,之的旨既昭而文字于以掀天揭地。

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诃萨,明相现时,从其住处来诣佛所,在外而立。尔时,尊者舍利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大目揵连、摩诃迦叶、摩诃迦旃延、摩诃拘絺罗,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从住处俱诣佛所,在外而立。佛知众会皆悉集已。尔时,如来从住处出,敷座而坐,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

昔如来于舍卫城敷座说法,与须菩提等演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喻法为名,以实相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其义甚深而明,其说甚简而切。昔有领悟一言之旨者即成正果。夫修六度万行以造夫真如之地,非由此经莫能以窥其径庭。盖万法本于一心,以心求道,道即是心。

尔时,世尊于中夜时放大光明,青黄赤白杂玻瓈色,普照十方无量世界。一切众生触此光者,皆从卧起,见此光明,皆得法喜,咸生疑惑:“此光何来普遍世界,令诸众生得安隐乐?”作是念已,于一一光复出大光明,照耀殊特胜于前光,如是展转乃至十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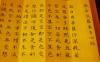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圣谛有四。此言是经何因何缘。佛世尊说如此经。云何圣谛有四不增不减。云何圣义及与谛义。若以圣故名为谛者。前二不应名谛。若言圣家谛故名为谛义则不定。复有经说。谛唯是一无有第二。云何四义而不破坏。复有经说。一切行法是名为苦。故唯二谛。四谛义不成。复次增一中说。

第3部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第538部 中阿含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摩伽陀国游波沙山,过去诸佛常降魔处,夏安居中与舍利弗经行山顶,而说偈言:“一心善谛听, 光明大三昧,彼人说妙法, 悉皆得充足,如渴饮甘露, 疾至解脱道。”时四部众平治道路,洒扫烧香皆悉来集,持诸供具供养如来及比丘僧,谛观如来,喻如孝子视于慈父,如渴思饮,爱念法父亦复如是。

论曰成立九种义句已。此般若波罗蜜即得成立。七义句者。一种性不断。二发起行相。三行所住处。四对治。五不失。六地。七立名。此等七义于般若波罗蜜经中成立故名义句。于中前六义句。显示菩萨所作究竟。第七义句。显示成立此法门故。应如是知。此般若波罗蜜为佛种不断故流行于世。

这首偈的大意是说:当菩萨(发大心的修行者)见到论议人时,就会发愿,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以佛陀的正法,摧伏外道的邪见和论议。见论议人:“论议”是说通过问答的形式等,分别阐述诸法的义理。其目的是使对方了解论理,明了法义,重在显明真理。佛在世时,比丘们常常就某一义理或论题等展开论议。著名的迦旃延尊者就是因为思惟敏捷,辩才无碍

这一愿的大意是说:当菩萨(发大心的修行者)见到身无铠甲、手无兵仗的军人时就会发愿,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永远舍离不善的身口意三业,趣于善道。见无铠仗:“铠”即铠甲。古时战斗中穿戴的铠甲战衣,可以防身。“仗”是弓、矛、剑、戟等兵器的总称,即兵仗、器仗。

此时世尊思维此梵志性格儒雅纯善质直,常为了求知而来请问,不是来惹麻烦的。他如果要问应当随意回答。佛就说:犊子。善哉善哉。随意提问吧,我会回答的。

这时世尊告诉憍陈如:色是无常。因灭色而获得解脱常住之色,受想行识也是无常。因灭此识而获得解脱常住之识。憍陈如。色即是苦,因灭此色而获得解脱安乐之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憍陈如。色即是空,因灭空色而获得解脱非空之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居士问:《金刚经》上说:“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何理解请师父开示!一如师父答:把所有的虚妄,就是一切相都是因缘和合的,所有的像都是生灭的变化的,无常的,他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对我们众生来说第一个就是破相证性。因为相是一个虚幻,因缘和合的假象。

迦叶菩萨说:世尊。一切法的意思不确定。为什么呢?如来有时说是善不善。有时说为四念处观。有时说是十二入。有时说是善知识。有时说是十二因缘。有时说是众生。有时说是正见邪见。有时说十二部经。有时说即是二谛。

善男子。虚空之性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佛性也一样。善男子。虚空非过去,因为无现在。法如果有现在则可说过去,因无现在所以无过去,也无现在,因为无未来,法如果有未来则可说现在,因无未来所以无现在也。

《宝积经》与《般若经》、《大集经》、《华严经》、《涅槃经》,并称为大乘佛教经典『五大部』,在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经以大乘经典的『空观』思想为基础,累积了《阿含》以来的佛陀教义,同时,也强调『无我』的思想与瑜伽的修行等,是中观学派及唯识学派共同尊奉的经典。

《四十二章经》是由后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同译的。后汉是指汉朝的东汉时期。汉朝共分两个时期,一是西汉时期,二是东汉时期。东汉时期又称为后汉。本经的翻译者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汉明帝因夜梦金人,于是派蔡憎和秦景、王遵三人带着十八个人到天竺求法,在求取《四十二章经》之后,遇到

如来佛性有二种:一有,二无。所谓恶有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力四无所畏,三念处大慈大悲,首楞严等无量三昧,金刚等无量三昧,方便等无量三昧,五智印等无量三昧,这都叫做有。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