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识的世界里,基本的东西世亲总结为一百样,分为五类,即所谓“五位百法”。第一位心法,就是上述作为“能变识”的八识,其余四位分别是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而说到底,后四位并没有能变之外、脱离心识的实存。世亲的论著中有《百法明门论》一卷,玄奘的传人窥基曾为作解,称之为“论主急于为人,而欲学者知要也”(注:《百法明门论解》,金陵刻经处,页一左。);此“要”乃是提纲挈领之要,尚非精微枢奥之要,其实是一张概念清单,本文甚短,不妨照录:
第一心法,略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入阿赖耶识。
第二心所有法,略有五十一种,分为六位。一遍行有五,二别境有五,三善有十一,四烦恼有六,五随烦恼有二十,六不定有四。
一、遍行五者:一作意,二触,三受,四想,五思。
二、别境五者:一欲,二胜解,三念,四三摩地(可译作“定”),五慧。
三、善十一者:一信,二精进,三惭,四愧,五无贪,六无嗔,七无痴,八轻安,九不放逸,十行舍,十一不害。
四、烦恼六者:一贪,二嗔,三慢,四无明,五疑,六不正见。
五、随烦恼二十者:一忿,二恨,三恼,四覆,五诳,六谄,七骄,八害,九嫉,十悭,十一无惭,十二无悔,十三不信,十四懈怠,十五放逸,十六昏沉,十七掉举,十八失念,十九不正知,二十散乱。
六、不定四者:一睡眠,二恶作,三寻,四伺。
第三色法,略有十一种。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色,七声,八香,九味,十触,十一法处所摄色。
第四心不相应行法,略有二十四种。一得,二命根,三众同分,四异生性,五无想定,六灭尽定,七无想报,八名身,九句身,十文身,十一生,十二住,十三老,十四无常,十五流转,十六定异,十七相应,十八势速,十九次第,二十时,二十一方,二十二数,二十三和合性,二十四不和合性。
第五无为法者,略有六种。一虚空无为,二择灭无为,三非择灭无为,四不动灭无为,五受想灭无为,六真如无为。
以上“百法”,对初读者来说,有些可以望文想义,有些则不知所云,为免枝蔓,这里不能一一说明,只能就其类别和某些要点略作解释或例示。
心所有法,省称心所,又作心数,约略相当于、但大大宽广于心理状态、心理机能云云。状态、机能之类,通常是用形容词或动词表示的,与用名词表示的“物体”有别;但在佛学里,状态、性质、物体等等,统统叫做“法”(Dharma);“法”者轨持义,只要有点确定性、可以辨识分别的对象,统统属于“法”。“万法唯识”的意思是:“外境随情而施设故,非有如识;内识必依因缘生故,非无如境。”外境不象内识那样是有,故外境无;内识不象外境那样是无,故内识有。“境依内识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识是假境所依事故,亦胜义有。”(注:《直解》,第12页。)外境也可说它是有,但那是“世俗有”;外境必须依托内识才能变现,所以内识是“胜义有”。在内识非无、且胜义有的范围内,将心所有法,当作“东西”、当作“物体”来理解,较之理解为性质、状态、机能,更符合唯识原义。而在外境非有、唯世俗有的范围内,一切法都无自体,都只是假象,换言之,根本不存在“有体之物”,不存在“物体”。
内识胜义有,而“有”的方式,“有”的程度,又各各不同,《识论》对此分疏精详。如烦恼心所(又称恶心所)中,贪、嗔、痴(即无明)三者作用最为强盛,“起恶胜故”,(注:《直解》,第391页。)最难伏断,所以立为三不善根。然则与三不善根相对的善心所无贪、无嗔、无痴,是否可以立为三善根,以表明它们也有深度的存在呢?于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义:无痴即慧为性。”(注:《直解》,第390页。)这种看法以为无痴的本性即是别境心所的“慧”,“为显善品有胜功能,如烦恼见,故复别说”,(注:《直解》,第390页。)只因为慧表现在善的方面、对善的增长有强大作用,就跟恶见(即不正见)对烦恼的增长有强大作用一样,所以另立一目善心所“无痴”;这等于说,无痴虽善,却不是根,非但不是根,连自己独立的存在都没有。但是另一“有义”则认为:“无痴非即是慧,别有自性,正对无明,如无贪、嗔,善根摄故。”(注:《直解》,第390页。)无痴是无明的对立面,与无贪、无嗔一起,成为三善根。这种看法采用“圣言量”为证明方法。《瑜珈师地论》中有一句话:“大悲,无嗔、痴摄,非根摄。”(注:《直解》,第390页。)句中的“根”字明确指慧根;佛的悲愿,属于无嗔、无痴,但不属于慧根;如果无痴以慧为性,岂非佛之大悲,应该属于慧根了吗?这就与《大论》所说相矛盾了。“又若无痴,无别自性,如不害等,应非实物,便违论说十一善中,三世俗有,余皆是实。”(注:《直解》,第391页。)《大论》中明明说,十一善心所中,除了不害、不放逸、行舍三者,它们是世俗有,(注:此处的“世俗有”,与大分类中与“胜义有”对立的“世俗有”应有区别;是内识胜义有的范围内、“有”的方式稍欠定实的意思。说到翻译的难处,陈寅恪曾谓:“此方名少”。猜想梵文原本中,此类细微的区别应较易表示。)其余都是实有;如果无痴以慧为性,别无自性,那么它应该和不害等一样,不是实有,这就又与圣言矛盾了。所以此“有义”的结论是:“由此无痴,必应别有。”(注:《直解》,第391页。)《识论》中各种“有义”的辩难,每每细腻如斯,注意及此,兴味无穷。
色法,约略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物质。通常人们对物质的认识多着重于质碍性,所以上物理课时要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场”、“引力场”之类也理解为“物质”就有点困难;但唯识学里相当于质碍性的,只是十一色法中的一法——“触”。作为色法的眼、耳、鼻、舌、身,并非作为心法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的重复;眼等五识是各自根、境、识三分的总和,而眼等五色只是其中的一分,即眼等五根,可相当于、但又并不等于眼睛、耳朵等肉体器官,眼耳等肉体器官另有一个名称叫“扶根尘”,佛教轻视肉体,等如尘土而已;根则主要克就其精微的变现机制为言。根是能缘,境是所缘,故境有客观对象的意思,眼等五根之所缘即色、声、香、味、触五境。五根、五境,皆属色法。范围最广的是第十一色法——“法处所摄色”,即“法处”所包括的一切“物质”。这里“法处”是指意识所缘的境。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触,如是,则意“对”法。眼等五识所缘之境的成立,必有赖于意识的参与,然而克就纯粹的意识而言,其所缘之境并不在外,故色法又分“有对”和“无对”两类,前十法属“有对色”,“法处所摄色”则属“无对色”。(注:不妨将“有对”、“无对”之分,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区别“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作个比较。洛克会特色、声、香、味归于“第二性的质”,因为它们乃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颜色是光波的主观反映,声音是空气波动的主观反映,等等,没有主观感觉的参与,就不会有颜色、声音等;而形状、大小、坚固性则是“第一性的质”,没有人和动物的世界里,不会有颜色、声音、香臭和滋味,但仍然会有方圆、长短、坚硬和柔软。若用佛语“格”洛克之义,则色、声、香、味固是“有对”,但“触”因为是“第一性的质”,就只能属于“无对色”了。可见洛克很不彻底。洛克后来的经验主义者贝克莱、马赫诸人,根本不承认“第一性”、“第二性”之别,在他们看来,“存在即是被感知”,一切都是“感觉要素的复合”,所以给他们贴的标签是“主观唯心论”,那么,唯识的标签可以同黑格尔一样,是“客观唯心论”了。如果说,唯识学所唯之心即阿赖耶识,则黑格尔所唯之心又在哪里呢?依鄙见,真不如用佛语说,贝克莱等人是“有执的唯心论”,唯识学是“无执的唯心论”,比较切当。)然而意根何在?意根却并不如眼等五根属于色法,并没有其“扶根尘”;照现在的认识强为之说,意根之扶根尘应该是脑,但唯识学里并无脑这个东西。意识其实是以末那识为其“根”,意根即末那识。末那识是重要性仅次于赖耶识的心法,当然不属色法。这是唯识结构的一个要目,下文当详。
就常识的理解来说,唯识论最大的难点在于要把“色”归结为“识”,致于认识到唯物论最大的困难在于要把“识”归结为“色”,则需要比常识深一层的提问。小乘佛学的“我无法有”,“我无”这一层意思极关佛教宗旨,在小乘也是积极主张的;但“法有”这一层意思,小乘似乎是无可奈何,不得不承认;铜墙铁壁挡在眼前,没有一直往前冲,头破血流也不顾的勇气,说它是无,实在说不出口。小乘说“法有”,归根结底是说“极微”(犹今之原子、基本粒子)有,“极微”是“能成”,色法(主要是有对色)是“所成”,所成即使无自性,能成却怎么说也应该有。《识论》于是作一大片文章,专门来评破“能成极微”。此片文字首先从极微有没有质碍、有没有方分、极微是不是处于“共和合位”诸方面,揭露许有极微将会造成的理论上的矛盾和过失,由此证成极微“定非实有”。然后精辟地指出:“然识变时,随量大小,顿现一相,非别变作众多极微合成一物。”(注:《直解》,第69页。)识的“能成”和“所成”,并不需要通过“极微”,以为中介,“极微”是个多余的概念,唯识的结构中没有“极微”的地位。
但是,为什么佛的教言中也有“极微”一语呢?回答是“为执粗色有实体者,佛说极微,令其除析,非谓诸色实有极微。”(注:《直解》,第69页。)佛说极微,也是方便假言,目的在于破除执“粗色”实有的谬见,本质上极微与形形色色的粗色一样,都非实有。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话:“诸瑜珈师,以假想慧,于粗色相,渐次除析,至不可析,假说极微。虽此极微,犹有方分,而不可析,若更析之,便似空现,不名为色,故说极微,是色边际。”(注:《直解》,第69页。)将“瑜珈师”三字改为“科学家”,这段话简直就是微观物理学一幅维妙维肖的写照。物理学家分析物质至于原子,并研究出原子的结构像太阳系,原子核居中,是太阳,核外电子绕核旋转,是行星,此是“犹有方分”的“极微”;进而,量子力学取消了轨道概念,电子在核外是以能级分布,不是沿轨道绕行,则此时已无“方分”可言;表征微观客体性状的诸“量子数”,其意义只能在数学结构中确定,晚近物理学家更将核子“析”为“夸克”,夸克的性质无以名之,假言色、味,而有“色夸克”、“味夸克”之称。至此,再要用常识的物质观来“格义”微观客体已绝不可能。《识论》说极微是“色边际”,细味之,不能不叹为神来之笔。陈真谛译《俱舍论》,极微译作“邻虚”,同样妙不可言。色处不虚,虚处无色,两间何有,假言极微,望色曰边际,望虚曰邻居;文字之精确雅驯,至此极矣。粗糙的说法往往引用科学,作为唯物论的论据,事实却是,科学至今的路向早已表明,科学不能、且无意于将精神归结为物质,科学不能、且无意于代替精神现象学,倒是科学对物质结构穷原竟委的探究,使得物质越来越不象物质了。借用标榜“中立一元论”的罗素的说法:“物质正在丧失其物质性,精神正在丧失其精神性。”小乘说“我空”,是空却个体人的精神性;大乘又说“法空”,更空却极微之类的物质性。但佛学并不主张另一种本体论(罗素则以所谓“原子事实”为本体),或者说佛学的本体论就是一句话:无本体。
唯识学区分“胜义有”和“世俗有”,很多时候也说“实有”和“假有”。唯识说理的要义在于免除“增减二执”:不知其假,而执假为实,是为“增执”;知其假,而承认假有,可免“减执”,“恶取空”就是一种“减执”。实有与假有、胜义有与世俗有,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划分,就像家用电器上的键纽,有些是ON/OFF双状态,有些是区分较细的格档,有些则是连续性的数字标度。这层意思在“心不相应行法”的建立上表现得十分明显。相望于瓶、衣等决定是假非有的外境粗色,“得”、“非得”、“命根”、“众同分”等等对说明唯识义理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应说为有,但相望于心、心所法,以及按唯识理解的色法,则得、非得等又不如它们实有,应说为假有。“心不相应行法”这个名称,已经表明,这些“法”与其他林林总总的内识不同,内识总是在心、心所、色法的相应关系中生起的,而得、命根、众同分等则不是;之所以称为“行法”,是因为佛教早有“五蕴”之说,而这些“法”都可为五蕴中的“行蕴”所摄。“行”者造作义,“心不相应行法”就是在心、心所、色法之“分位上假立”,造作而成的。造作可,执著造作,以为实有,则不可。
例如关于“得”,人们如成语所说“患得患失”,就是将“得”与“非得”执实了。小乘也执“得”与“非得”为实,小乘有义还引经说:“补特伽罗成就善恶,圣者成就十无学法”,“异生不成就圣法,诸阿罗汉不成就烦恼”(注:《直解》,第77页。),以为这些经文可以证明“得”有实体。《识论》破斥其“为证不成”,经过一套严密的说辞后总结说;“依有情可成诸法分位,假立三种成就:一种子成就,二自在成就,三现行成就。翻此,假立不成就名。”(注:《直解》,第78页。)成就(得)、不成就(非得)都是假立,功名利禄,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什么得不得?但是仍然对“得”与“非得”之类作一个安顿,将它们列为“心不相应行法”,纳入内识范围,假有为内识所变现的意思就突出了。又如关于“众同分”(即众生的共性),小乘也是引经说为证。《识论》指出其“为证不成”后,设言:“若同智言,因斯起故,知实有者”(注:《直解》,第80页。),如果因为众生都有智力和语言而说众生有共性,那又怎么样呢?回答极其巧妙:“若于同分起同智言,同分复应有别同分。彼既不尔,此云何然?”(注:《直解》,第80页。)如果智力和语言相同还不够,必须另有共性为其基础,岂不是这个共性也须有别的共性为其基础吗?这样就陷入了无穷递推,止于胡底?可见“同分”也就是某些事物的某些方面相同而已,“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差别,假立同分”(注:《直解》,第81页。),并非另外实有一个同分之体。小乘与大乘关于不相应行法的看法分歧,颇同于西方哲学史上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
世亲造《俱舍论》,已开列十四个不相应行法,造《百法明门论》,又增加至廿四个,《识论》行文中是为批评小乘执不相应行法实有的观点而分别论说该位诸法的,对增加的诸法则未作具体论述,只一言以蔽之:“执别有余不相应行,准前理趣,皆应遮止。”(注:《直解》,第94页。)而我们倒不妨尝试用唯识观点对省略的部分作些思考。例如其中的“时”、“方”二法。“时”是时间,“方”表空间。常识的观点没有办法不把时间和空间看作实在和实有,即使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任何东西在里面,空间和时间也存在着;但是唯识论却将其看作“行法”,即造作之法,所以是假有。这与康德的时空观倒能够相通。康德视空间与时间为“直观的形式”,“属于我们心灵的主观的‘造性’”。(注: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2页。)康德承认“作为我们一切经验的条件”,时空具有“经验实在性”,但是否认时空具有“绝对实在性”,“时间无非是我们内部直观的形式。如果我们从内部直观除去我们感性的特殊条件,时间这个概念也就消逝了;它并不依附于对象,而只依附于能直观对象的主体。”(注:《纯粹理性批判》,第75页。)梁启超读康德,将时空直观、知性范畴喻为有色眼镜,述康德意为“一切之物皆随眼镜之色以为转移”(注:转引自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8、89页。),可谓既形象生动,又准确到位。唯识曰“行法”,康德曰“造性”,连用词都相同。所不同者,康德的“造性”有明确的主体,唯识则并此主体也作为“假说之我”而消解空却了。
《婆薮?豆法师传》里,无著请弥勒菩萨为众说法,“弥勒即如其愿,于夜时下阎浮提,放大光明集有缘众,于说法堂颂十七地经,随所颂出随解其义”,白天弥勒回到他住的兜率多天,“无著法师更为余人解释弥勒所说”,这样“经四月夜解十七地经方竟”。(注:《婆薮?豆法师传》,新修大正藏经,卷50,第188页。)兜率多天与阎浮提相距遥远,弥勒菩萨夜出早归,如同普通人上夜班,在普通人看来,弥勒是具有特异功能,他像飞机、火箭克服实在的空间距离一样,能每天两次克服天地之遥,只不过他的功能更大,几乎能够瞬息千里。这种见解,视空间距离为实有,须有异常的功能去克服它,但在唯识论看来,空间距离本非实有,只要不造作生起,它便无由假立,自然对治它也无须什么功能。佛书中极多能令众生舌挢不下的神奇事迹,但其讲法却往往像讲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毫无特异功能的意思。质言之,“功能”一词,在唯识学里并不表示主体的能力,只是“种子”而已。杂染法也有种子,只有伏断了杂染种子,人才能回归正常,佛菩萨只是正常人而已,何有于特异功能?金克木先生对印度古代文学作过一个极其精辟的概括,叫做“概念的人物化”。佛经里的“神话”,如果我们从其背后的义理去解释,把“神话”只是看作义理的形象化,神奇也就化解了。
唯识的基本结构是见相二分,能所二取。世界上的我法种种,都是变现、分别的结果,而所谓“变现”,所谓“分别”,就是变现出“见分”和“相分”,分别出“能缘”和“所缘”。《识论》上说:“然有漏识,自体生时,皆似所缘、能缘相现;彼相应法,应知亦尔。似所缘相,说名相分;似能缘相,说名见分。”(注:《直解》,第149页。)不妨说,见分、能缘,表示主观的方面,相分、所缘,表示客观的方面。但通常的主客二分,只把“心”放在主观一边,而在唯识,则主客两边都是心分。梁漱溟先生体会得好:“一般所说的心但是半边的,唯识家所说的心是整个的。一般所说的心但是那作用,唯识家所说的心是个东西。”(注:《唯识述义》,见《梁漱溟全集》卷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梁先生体会到的这个意思,《识论》上是这样说的:“变谓识体转似二分,相见俱依自证起故。依斯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注:《直解》,第9页。)又说:“达无离识所缘境者,则说相分是所缘,见分名行相,相见所依自体名事,即自证分。”(注:《直解》,第151页。)缘作动词时,有缘托、缘虑、认取的意思;相分是所缘,有对象的意思;见分是能缘,有主动作用的意思,这个主动作用,又叫做行相。任何心识的变现、生起,都是见分缘取相分的结果,必须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因此相分和见分必须有它们的共同“所依”,就是自证分。自证分作为“相见所依自体”,当然“是个东西”,当然不是单边的作用。《识论》又名自证分为“事”,在唯识家看来,心外无事;悠悠万事,无非心事,心中有事,“转似二分”,见分取相,完成心事。相、见二分是难陀的说法,相、见、自证三分是陈那的说法。二分说尚易致误解,三分说则已经将心识坐实为“整个”的“东西”了。后来护法又提出四分说,于相、见、自证之外,更立一个“证自证分”。四分说“微细难讲”(梁漱溟语),此处从略。事实上,《识论》对二分、三分、四分各说虽都有开列,但贯穿于具体论述中的,基本上是二分,因为只要不把相分推出去,执为离识外在的实有,作为唯识结构的纲领,见相二分是足够了。
唯识结构的基础和大本营是第八识。第八识有多种“相”,不同的相,受有不同的名称。常说的“阿赖耶”,为其“自相”,阿赖耶是藏义,故第八识又称“藏识”,表明一切种种的事件、现象、心识,都从这里酝酿和生发。第八识还有“因相”和“果相”,“因相”叫做“一切种识”,“果相”叫做“异熟识”。“异熟识”专就生死轮回而立名,“种识”则专就一切法、一切事都由其自身的种子生起,而种子无论本有抑或新熏都由此识摄藏而立名。三相分别,其体则一,并且三相的作用也总是互相贯通,彼此合作的。例如异熟识,有情众生在他的一期生命中,现行种种善恶之业,都会种因在此广大识田上,感生着异熟果,“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如何不失不得呢?就是因为此识能藏一切种。“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俱,前异熟既尽,复生余异熟。”(注:《直解》,第564页。)此所谓“习气”,就是种子。习气又分业习气和二取习气,业习气就是有情所造现行种种善恶业形成的新种,直接感生着异熟果;二取习气则是无始以来藏识中本俱、总要表现出见分与相分、能缘与所缘的种子,对感生异熟果只起辅助作用。“二取种受果无穷,业习气受果有尽”,(注:《直解》,第565页。)二取习气是无穷无尽的,在生死相续的异熟果系列中始终存在,业习气只对一期的异熟果起作用,“前异熟既尽”,一期生命受用尽了,新的异熟果也就异地而熟了,“复生余异熟”。这样的循环轮回只是有漏的第八识的行相,佛菩萨伏断了所有的杂染种子,第八识成了“净种识”,也就不再有异熟一相,出离了生死相续的轮回过程。种子当然不仅限于感生异熟果者,“此中何法名为种子?谓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注:《直解》,第121页。)一切有为法都有种子,望种而言,一切有为法都是果。佛家说四缘: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其中,因缘就是种子,种子就是因缘。假法如魔术、梦境等没有种子,但假法作为心识的相分,此心识之生起,有其种子。玄奘所宗护法、戒贤一系,坚决认为阐提种姓不能成佛,就是因为其本识中不存在有为无漏的本俱佛种。
业报、轮回甚至涅?,其实都不是佛教的特创,而是佛教之前古印度的普遍思想。例如数论派就主张有“神我”,神我不死,以思为体,灵妙难言。肉体生命结束以后,神我借尸还魂,就是轮回;如能修行到远离一切,神我独尊,就是涅?。其他还有自我、他我、即蕴我、离蕴我等等各说,总之是有我。佛陀初转*轮,针对这些种种异说,说三法印,第一印即是“诸法无我”。佛陀教理,在无我的大原则下,对轮回、业报的观念作了根本性的改造,至唯识学而形成一个无远弗届、靡细不入的理论体系。唯识学在异熟识上说生死相续、业报轮回,无我的宗旨就贯彻于其中了。“我谓主宰”,这世界没有主宰,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也没有主宰,最要紧的是:即使阿赖耶识,也不能解释为“我”,解释为“主宰”。《显扬圣教论》说:“阿赖耶识者,谓先世所作增长业烦恼为缘,无始时来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为体。此识能执受了别色根、根依处及戏论熏习,于一切时一类生灭不可了知。”(注:《藏要》卷10,130页。)有情的生死,它压根就不知道。《识论》论阿赖耶识:“此识行相,极不明了”,“此识任运,无所希望”,“此识懵昧,无所印持”,“此识昧劣,不能明记”,“此识任运,刹那别缘”,“此识微昧,不能简择”,(注:《直解》,第175、176页。)那里有什么“我”义、“主宰”义在其中呢?金克木先生说得好:“有此存储业报种子之巨库,乃可释业报,解轮回,而无需一‘神我’;无我、无常、刹那生灭之教可仍持不失矣。”(注:《说“有分识”》,见《梵佛探》,河北教育出版杜1996年5月版,第435页。)但是常途对佛教轮回思想的理解,却又大大地歪曲了,恰恰回到了佛教最要批判的有我论;今生受苦受难,来世荣华富贵,仿佛真的另有一个不死之“我”在那里出生入死。种子、果报这些名词,可能是从水果植物那里借用来的,但是意义结构实有根本的区别。长成这个苹果的种子来自那个苹果,两个苹果之间有因缘关系,至少在基因上,子苹果保留着父苹果的特征。但在前后异熟果之间却不是因缘关系,异熟果的因缘(确切地说:种子)是种在异熟识里,而不是包裹在前异熟果里,前后异熟果里,并没有一个起主宰作用的不变不死之我。
笔者读到过一本《佛教哲学》,里面说:“最为尖锐的问题是:原始佛教整个思想体系所包含的理论矛盾和理论危机:无我与轮回如何统一呢?人们的认识活动需要统一,由谁来主持呢?人们的记忆又由谁来保存呢?人们的行为和获得果报,又由什么来负责和承受呢?部派佛教犊子部一系就主张有我,‘我’就是‘命’,就是生命的主体。”(注: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77页。)诚然,佛教的初期,在无我的大原则下还残留着一些有我论的痕迹,但这说不上是什么“理论矛盾”,更说不上“理论危机”。就像科学上初出现的新范式,必然会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新范式正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问题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从而得以丰富和发展,并得以最终确立。事实上,佛教发展至唯识学,无我与轮回的统一早巳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像“谁来主持”、“谁来保存”、“谁来承受”,这样子问题的提法,本身即是以有我论为前提,所以并不是对佛教自身问题的揭示,而勿宁说是站在有我论的立场对无我论的质疑,是在限定和逼迫着得出一个有我论的答案,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佛教的“思想体系”。就像现代宇宙学说时间有开端,用常识不能理解,于是执着地追问:“开端之前又是什么呢?”这样提问题没有意思。
佛教允许假说“我”,无我唯识的意思,若用假说之我与实有之识的关系来表达:是“识”上“皱起”(牟宗三语)了“我”,而不是“我”拥有“识”。佛说五蕴和合即是我,唯识又言五蕴皆不离识,所以是我以识成,而不是识依止我。世亲造《大乘成业论》对这层意思辩证得非常明白,也非常周到:“又于识等我有何能,而执我为识等依止?若言识等因我故生,我体恒时既无差别,如何识等渐次而生,非于一时一切顿起?若谓更待余因助力方能生者,离余因缘如何知有我能生用?若言识等依我而转,诸法才生,无间即灭,既无住义,容何有转?故不应执我体实有,与六识身,为所依止。”(注: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第29函,《大乘成业论》,第17页。)语言中似乎深植着有我思想的根底,一不小心,就说成了“我的识”、“你的识”,甚至“我的赖耶”,“你的赖耶”,于是我又成了主体,而六识甚至赖耶,反倒成了“我所”,就是唯识学的书中,也会有“有情各有赖耶”之类的话头,这些都是方便说法,在义理既明的言路中,倒也不必忌讳。
唯识的结构,还要从心与心所的相应、生起、依、缘这些方面作整体的把握。第八识因其“极不明了”、“懵昧”、“昧劣”等等性质,只能与遍行心所相应,与其他心所俱不相应。第七末那识是产生我执的根源所在,与之相应的心所,除了五种遍行心所外,最重要的是四种根本烦恼,即我痴、我见、我慢、我爱。上文列举的五十一心所中,根本烦恼有六种,其中不正见又可细分为五种,即身见、边执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故也可说根本烦恼有十种。与末那识相应的四烦恼中,我痴属痴,我慢属慢,我爱属贪,我见属身见;身见中另有一种“我所见”,连同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都是从我见中派生出来的,都不与末那相应,这说明末那识所俱的我见是最深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什么都见不到,就“见”到“我”。因为有“我爱”,所以没有“嗔”,最深处的爱,是不会有嗔的;因为我见坚定不移,没有丝毫犹疑,所以末那与“疑”也不相应。关于与末那识相应的其他心所,有多种“有义”,论辩复杂,此处从略。致于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则总共六位心所,都能与它们相应。
唯识学用相应心所的“生起”来说明心理状态。常途说心态如何如何,眼见财色而意有贪欲,唯识学却偏不说“心理处于贪爱状态”,而说“贪心所生起了”。常途的说法,都把心所的生起归到意识的性质,见猎心喜,见钱眼开,是思想意识造成的,贪欲是思想意识的毛病,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须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要对某种顽固的本性进行改造,此所以有“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之叹也。而唯识学论“心理状态”,只是那众多的心所在那里起起落落,有的生起,有的灭没,有的生起了旋即灭没,有的灭没了复又生起;有的生起后似乎长在,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灭没;有的灭没后久久暌隔,又焉知没有可能忽然生起。唯识学论修行,是要将所有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的心所之种子尽皆伏断,使它们永远不再生起。而不是要对什么本性进行改造,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本性。以改造本性来理解修行,不免又落入不正见之一的“戒禁取见”,是“戒禁取见”在生起了。
心与心所互相的“依”和“缘”,呈现出唯识结构的整体性。
“依”有三种。一是“因缘依”。心、心所、一切有为法都依“自种子”而生起,这自种子就是它们的因缘依。另一是“等无间缘依”。心识生起后,往往会持续存在,彻底的性空之义决不许将任何东西的持续存在理解为自身等同的延续,而只能是“前念灭已,后念旋起”,只能是同类心识的相继生起,在前的心识等流无间地为在后的心识开路,前心识便成为后心识的等无间缘依,又叫做“开导依”。“有义”颇多的是“俱有依”(又叫“增上缘依”),而《识论》认为正确的有义是:眼等五识的俱有依,“定有四种,谓五色根、六七八识”;“第六意识,俱有所依,唯有二种,谓七八识”;“第七末那,俱有所依,但有一种,谓第八识”;“阿赖耶识,俱有所依,亦但一种,谓第七识”。(注:《直解》,第275页。)因缘依说的是因果性,等无间缘依说的是历时性,俱有依的讨论则为唯识的整体结构画出了一幅同时性的轮廓,其中第七、第八二识是互为所依。
《识论》对于唯识结构中“所缘”的讨论,最能体现唯识学以立为破、破在立中的基本精神:通过彻底说明“我执”之所从来,达到破斥我执的目的;犹如通过揭示魔术的机制,达到“拆穿西洋镜”的目的。《识论》区分我执为“分别我执”与“俱生我执”两种。比较而言,分别我执浅一些,是“见所断”。俱生我执则必须通过持之以恒的修习,才能破除,所以说是“修所断”;与末那识相应的“我见”即是俱生我执。然则“我见”究竟“见”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见到了“我”,因为“我”是没有的。“我见”是将第七识的“所缘”执实了,才形成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所以问题是:第七识的所缘是什么?
这个问题上也有多种“有义”。有说末那识的所缘是第八识的见分与相分,“如次执为我及我所”:有说末那识的所缘是第八识与它的种子,“如次执为我及我所”。这些都是不透彻的见解。在“我”与“我所”的对待中执我,仍然不是最深刻的我执。玄奘赞成的“有义”问道:末那识“俱萨迦耶见,任运一类恒相续生,何容别执有我、我所?”(注:《直解》,第288页。)萨迦耶见即身见,与末那识相应的身见,是永远以相同的形态连续生起的,不可能“别执”两样东西,既执我,又执我所;所以正确的见解只能是“此意但缘藏识见分”,“此唯执彼为自内我”;(注:《直解》,第289页。)藏识是能变识的核心,藏识见分是核心中的核心,末那识以藏识见分为所缘,与末那相应恒转的我见顽固地将此所缘执为“自内我”,这就是我执的最深根源。人们可以想得通,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都不在我的范围内,但人们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会连我都不是我呢?”《识论》挖出了这个“想不通”的根子。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我思”是一种“我所”。唯识学则说:“我见(萨迦耶见)故我在”,“我见”也是一种“我所”。笛卡儿用“我所”坐实“我在”,唯识学则以“我所”说明“我执”的来源,归根是要证明“我不在”。分歧的关节点在于:笛卡儿的“我所”(我思)属于意识的层面,《识论》的“我所”(我见)属于比意识更深而为意识之所依的末那识的层面。好的医生治病,不是只对症状做治表的处方,而是揭露病根,对根施治。《识论》中如理建立的唯识结构,好比好医生所熟悉的解剖图,俱生我执的病根已准确定位,病理已清楚阐明,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执在道理上已被破除。又好比看懂了魔幻术背后的机制,也就等于破了这个魔幻术。但是,俱生我执不是见所能断,即使将《识论》读得烂熟,倒背如流,义理词句,分毫不差,我执也可能依然故我。关于末那识,世亲颂言“思量为性相”,末那识以思量为自性,复以思量为行相,故末那识又名“思量识”。(注:葛兆光先生著《中国思想史》,屡屡声言以写历史上的“一般思想”(而非“精英思想”)为主,这并不妨碍他在第二卷中也写到了唯识学。短短两三页的篇幅,错误百出,不知所云,有的简直是胡说。例如第123页的一句话:“因为种子有‘能变’,所以由于熏染,众生不能保持阿赖耶识的自我本原状态,于是经由末那识转入意识界,即‘思量识’,于是由各种感觉色声香味触,经眼耳鼻舌身五识构成了心中的种种幻象,对一切众相有了‘了别境识’。”在用最少的字句制造最多的错误和混乱方面,这句话大概可以创记录了。种子与能变的关系,明明是种子为“初能变”即第八识所摄藏,是种子在能变里面,怎么成了“种子有‘能变’”呢?阿赖耶识本身的性质虽然是“无覆无记”,但所摄藏的种子却是染净都有,其“本原状态”是“与杂染互为缘”,众生恰恰最能“保持”(其实是难以改变)这种状态;只有修行到家的人才能断掉染种,改变赖耶识的状态,使“一切种识”成为“净种识”。“眼耳鼻舌身五识”(还有意识),统称为“了别境识”,说“经眼耳鼻舌身五识……有了‘了别境识’”,这算什么句式?“内识非无如境,亦胜义有”,所以像“心中的种种幻象”这种词组,在意识流或后现代小说中可以尽管用,用来述唯识义,未免太不严肃。我敢说,葛先生对唯识学的经论,一页都没有读懂,否则怎么会把“意识界”说成“即思量识”呢?错得实在太离谱,太荒唐了。葛先生自己也引过《识论》开篇的偈颂:“此能变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明明白白交代清楚了能变识的名称:初能变第八识名“异熟”,次能变第七识名“思量”,第三能变前六识名“了别境识”。《识论》论完第八识,在卷四的中间开始论第七识,出句便是:“次初异熟能变识后,应辩思量能变识相。”葛先生的这个错误无法用“硬伤”、“疏忽”来解释,怎么解释,下走也想不明白,因为这等于是:一再告诉你,鄙姓陈,草字克艰,你还要说鄙人的名字是余秋雨。致于什么“经由末那识转入意识界”这样的话,我又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懂,包括葛先生自己也不懂;葛先生令人佩服的本事是,把自己也不懂的话写下来印成书。葛书虽然严格遵守引文注出处的规矩,但是像这样凭胡思乱想而望文生义、靠瞎七搭八以拼凑词句的后派作风,下走看来,实在太不符合学术规范。)“未转依位,恒审思量所执我相;已转依位,亦审思量无我相故。”(注:《直解》,第292页。)众生有病,是“未转依位”;阿罗汉病瘥,是“已转依位”。唯识的教理行果,最终落实在“转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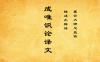
成唯识论译文 卷第一:外人难说:如果只有识的话,为什么世间的一般凡夫及诸外道和出世间的诸圣教都说有我、有法呢?论主回答说:《唯识三十颂》说:“我和法都是假设而有,有各种各样的相状,它们都是识变现的。能变之识只有三种:第八阿赖耶识为异熟识,第七末那识为思量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称为了别境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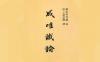
暂无简介。

成唯识论是成立唯识之论。唯识学建立于无着世亲。佛教在释迦世尊涅槃之后,最初声闻乘流行,以证得出世的阿罗汉果为目的。后来乃有菩萨乘兴起。以声闻乘不求成佛,为未到究竟,且其度人的方便亦不广大,因目之为小乘。而自命为大乘,广度一切众生。同登无上佛道。大乘先有龙树提婆所倡导的中观系,后有无着世亲所建树的瑜伽行系,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两

成唯识论讲解

题前概说 佛教唯识学,是门极有条理,极有系统,极有组织的学说,亦是一门极有高度,极有深度,极有广度的学说,不特在佛教各宗派的教义中,难见有可与之相匹敌的,就是在世间各种思想学说中,亦少发现有像唯识学那样的。是以今日时代思潮,不论有着怎样飞跃的进步,各种学说思想,不论有着怎样高度的发展,但唯识学仍然值得吾人学习。

阿赖耶识是唯识学建立的根据,万法唯识是依据它而成立的。长期以来对阿赖耶识得理解存在着许多歧义,由此所带来的对唯识的解释也种种不同。《成唯识论》作为唯识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对阿赖耶识的解释也是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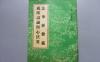
夫万法唯识。虽驱乌亦能言之。逮深究其旨归。则耆宿尚多贸贸。此无他。依文解义。有教无观故也。然观心之法。实不在于教外。试观十卷论文。何处不明心外无法。即心之法。是所观境。了法唯心。非即能观智乎。能观智起。则二执空而真性现。所以若境。

世亲菩萨作了《唯识二十颂》,并自作长行释之,名《唯识二十论》,以破外道小乘实有外境之邪执,而显唯识无境之妙理。其后又作《唯识三十颂》,未及作论而寿终。安慧、护法等十大论师,奋力研究唯识,并为此颂作释;玄奘西游,一一取回以授窥基,基师一一折衷取舍,糅集众说,以释《唯识三十颂》而成论。此论依境、行、果三分成立唯识妙义

彼等倡言:【但应了解《成唯识论》之见道位判果标准与萧老师建立是有所不同;《成唯识论》意为先伏二执现行方入初地,入地则断除种子。】 彼等如是主张者实有大过,谓不知己过之后,复又诬责于人,更增大

简明成唯识论白话讲记

一、《成唯识论》中的因果俱时 因果俱时是唯识学的特色理论,在《成唯识论》和《摄大乘论》等经典中有相关表述,为之前的佛教学说所不具备。《成唯识论》共十卷,为护法等造,唐代玄奘翻译。又称《唯识论》、

(韩国)高荣燮 着 张惠文 译一、 问题与构想 围绕佛教识、心展开的论辩成为7、8世纪东亚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心识之辩主要探讨人的意识究竟是八种还是九种,也称八识九识论或八九之辩。[1]这时期

‘山中十日西湖别,堤上桃花红欲然’:乃吾清明日从净梵院赴弥勒院,在湖中泛一叶扁舟,舟次偶然流露于吟咏者。夫桃花之红,莫知其始,山外之湖,湖上之堤,物皆位之有素。且吾非一朝一夕之吾,居乎山,游乎湖,玩春色之明媚,弄波影而荡漾,今岂初度?然人境交接,会逢其适,不自禁新气象之环感,新意思之勃生也!夫唯识论亦何新之有?然为欧

佛学素被人认作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第二源泉”。在中国佛学的诸流派中,大乘佛教的“唯识论”以其精致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堪称中国佛教哲学的开山,也正是由于唯识论,才有了华严宗、禅宗等业已中国化的佛学的中兴,才有了宋明新儒学的崛起,也才有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在现代中国的凸现。本文的主旨是把唯识论作为一种东方式的现象学理论与西方

唯识论内部存在着种种分歧,这是历来唯识论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成唯识论》一书保留了当时十家唯识学者的不同观点,现代的研究者、如印顺法师等则论述了唯识思想前后期一些重要变化。而笔者以为,唯识论前后期除了学术观点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外,更有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即从《解深密经》到《成唯识论》,唯识论经历了从否定世俗世间、

唯识思想前后期价值取向之重要变化 ——《解深密经》与《成唯识论》三自性理论比较 作者简介:林国良,1952年生,男,上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唯识学。 摘要:《解深密经》与《成唯识论》在三自性理论上存在着差异,包括遍计所执自性是否遍一切法、依他起自性能否依

《成唯识论》与《大乘起信论》熏习观的比较 秦 萌 一、《成唯识论》的熏习观 首先,我们先来看《成唯识论》的熏习观: 依何等义立熏习名?所熏、能熏各具四义,令种生长,故名熏习。何等名为所

《成唯识论》十卷 护法等菩萨造,玄奘译,是唯识宗核心典藉。《成唯识论》是《唯识三十论》的集注。《三十论》世亲菩萨撰。世亲是无著的胞弟,唯识学的集大成者,原在有部出家,不久便通达犍陀罗一带流行的有部教义,旋即研究经部,当时正统的有部思想在西北印的迦湿弥罗,由世友等领导的结集的《大毗婆沙论》保存那里,严禁外传

《成唯识论直解》观感漫谈 陈新 只要熟悉中国佛教史,乃至只要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无不知道《成唯识论》的重要性。但由于该书的难解,历来对该书的注疏寥若晨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二OOO年四月出版,林国良先生撰写的《成唯识论直解》(以下简称《直解》),在文字的梳理、义理

佛教论书《成唯识论》的注释书。亦称《成唯识论疏》,略称《唯识述记》。窥基撰。20卷(或作10卷、60卷)。全书分五门。①辨教时机。主要说明法相宗的三时判教和五种姓说的思想;②明论宗体。主要阐述以识有境无的唯识思想为宗,以“

《大般若经》六百卷,又称《般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朝玄奘翻译。这是有关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之著,所以卷帙浩繁。当年玄奘法师西域取经,取来此经本子有三种,后来进行翻译,碰到疑问,便就三本互校,殷勤省覆,择善而从,然后落笔,

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基本经典之一。唐玄奘译。五卷。除玄奘译本外,还有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北魏菩提流支、南朝陈真谛译的三种译本。该经的中心,是大乘的境行果,境指心境。一共八章,即:序、胜义谛相、心意相识、一切法相、无自性相、分别瑜伽、地波罗蜜、如来成所事。除序外,其余七章(品)是正文。正文前四章,讲“所观境”;中间二

成唯识论也叫《净唯识论》,简称《唯识论》,法相宗所依据的重要论书之一。印度世亲写了一部叫《唯识三十颂》的著作,印度护法等十位佛学理论家,对它进行了注疏讲解。玄奘综合了这十位理论家的注释,翻译写成了这本《成唯识论》。十卷。该论的内容:

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中、家庭里,若碰到对我们不友善,或专门找我们麻烦的人,都将之归类为恶人。我们要如何面对恶人呢?佛陀在他弘法的生涯里,也遇到一个大麻烦,就是他的堂兄提婆达兜。提婆达兜嫉妒佛陀的成就,要推翻佛陀,自己做领袖,以种种方法来陷害佛陀;

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原始佛教的统一教团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其后复细分为小乘十八部或二十部,各部派均各有其独自传承的经藏。依现今资料显示,当时至少有南方上座部、有部、化地部、法藏部、大众部、饮光部、经量部等所传的经典存在。

《阿含经》属于印度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性典籍。一般认为,此经基本内容,在释迦牟尼逝世当年,佛教节一次结集时,就已经被确定下来。然而有的文献,又把它看成为声闻乘三藏里的经藏。“阿含”,有的书里也译成为《阿笈摩》等,可能成为“法归”,“传承的说

听经闻法,好比生活中需要吃饭一样重要,为了身体健康必须吃饭,同样的,为了让慧命增长,就必须听经闻法。身体有病,医生会开药方为我们治疗;心里有病,则要靠佛法的阿伽陀药(能够普遍治一切病的药)来治疗。所以听经闻法时,要有「疗病想」。如:觉得自己有贪

三种恶的行为,衍生出来就是十恶行。这十恶行是身体犯杀、盗、淫;口犯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心、意犯贪欲、瞋恚、愚痴邪见等。在佛教讲,你不做十恶行就是十善行。有人说,我一生都没敢杀鸡、鸭,甚至一隻蚊子、一隻蚂蚁都没有敢打死,我不会杀生的。其实,一

布施有很大的功德,但布施若没有智慧或布施错误,就会有过失。例如:拿钱给小孩买刀剑玩具,玩惯以后,他可能会用真刀真剑去伤害人;买小鱼、小鸟给小孩子玩,一直玩到死,养成没有慈悲心,这也不好。买香菸送人、买酒送人、替人传递毒品、捕鸟送人、捕鱼送人、

什么叫「居家善知识」?家里的成员中,可以作为模范者,他就是家庭里的善知识;做先生的,因为太太的支持而有成就,太太就是先生的善知识;贞节贤良的妻子,是我们居家的善知识;具有正见智慧的老师,是学校的善知识;从事社会公益的好人,是社会的善知识。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