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第四 人間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汙世,出與人接,無爭其名,而晦其德,此善全之道。末引接輿歌云:“來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此漆園所以寄慨,而以人間世名其篇也。 正注謂人間世為當世,未盡其義。蓋人間以橫言,世以豎言。人間世者,謂人與人之間相接之時世也。世有三,即接輿所歌往世、來世、方今之世也。而人與人間之相接,不外乎於內則心,於外則形與行。本篇凡六節。第一節,孔、顏問答,致齊虛心以應世也。第二節,孔、葉問答,安命養心以應世也。第三節,顏、蘧問答,正身和心以應世也。第四節,匠石師弟問答,而足之以南伯之言,明物之寄形於無用,以免世害也。第五節,支離疏支離其形,明人之寄形於無用,以免世害,且蒙世益也。第六節,接輿卻曲其行,以避世也。如此數面寫來,人間世之義,無餘蘊矣。然皆莊子之寓言,藉以明其道要而已。而其道要,則在於事心。故一至三節,事心之正文也;四節之寄形於無用,能虛其心也;五六之支離其形,卻曲其行,免累其心也。如作孔、蘧諸人事實觀,則傎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釋文:“司馬云:‘衛莊公蒯聵。'按左傳,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顏回已死。此是出公輒也。”姚鼐云:“衛君,讬詞,以指時王糜爛其民者。” 補成疏: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奚,何也。之,適也。其年壯,其行獨,宣云:“自用。” 補釋文:“行,下孟反。獨,向云: ‘與人異也。'”武按:“年壯”句,為下“夫以陽為充”句伏根。輕用其國,役民無時。 補輕率用其國之權 力。而不見其過,郭云:“莫敢諫。” 補不自覺其輕用之過。輕用民死,視用兵易。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慘也。郭嵩燾云:“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蕉萃',班固賓戲作‘焦瘁'。廣雅:‘蕉,黑也。'” 正量,比也,度也。則陽篇云:“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荀子富國篇云:“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注:“猶穀量牛馬。”澤,風俗通:“水草交厝,名之為澤。”蕉,釋文:“似遙反。向云:‘蕉,草芥也。'”呂氏春秋審應覽不屈篇:“蕉火大钜。”注:“蕉,薪樵也。”列子周穆王篇:“覆之以蕉。”注:“與樵同。”此句言以國內死者之數,比量於澤,若澤中草薪之多焉,猶言死人如麻也。此乃找足上“輕用民死”義。注訓蕉為焚焦,非是。章太炎云:“國不可量乎澤,當借為馘,以馘則可量乎澤也。”說似是而非,且蹈擅改原文之失。此為清代訓詁家之通蔽,非武所敢苟同也。須知此為倒句法,如將“以國”二字置“死者”二字之上,則為以國之死者量,非以國量也。足知改“馘”之不必矣。民其無如矣。無所歸往。 正非。秋水篇:“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言予使一足,尚無如之何,今子使萬足,獨奈之何哉?此句與“予無如矣”同一句法,謂民無如衛君之暴何也。又戴震云: “魯論‘吾末如之何',即‘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為那。”武按:玉篇:“那,何也。”廣韻:“ 那、奈通。”則民無如矣即民無奈。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所事。”亂國就之,宣云:“欲相救。”醫門多疾。'入喻。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則,法也。”補願以所聞于夫子者,思其醫國之法。應上“將之衛”句。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愈也。” 補釋文:“瘳,醜由反。”言庶幾其國如疾之愈,而不再輕用乎!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汝也。往恐被戮。” 正釋文:“嘻音熙,又於其反。”成云: “怪笑〔一〕 聲也。”武按:殆,將也。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憂患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己尚不能立,焉能救物?”補“雜”“多”“擾 ”三字,反伏下文“定”“一”“虛”三字,而“一” “虛”二字,為全節主腦,餘字則□索也。蓋道不雜則一而不多,不多則不擾,不擾則定,定則虛,虛則所以集道也。故定者一之效,虛者定之效;雜多為一之反,擾為定之反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立也。” 正存,當為 “成性存存”之存。爾雅釋詁:“存,在也,察也。” 楚辭遠遊篇云:“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於此“存”字之義最合。此“存”字,隱攝下“心齊”義。下文云:“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蓋能存諸己則不馳矣。然則謂心齊之工夫在一“存” 字,亦無不可。老子之“綿綿若存”,亦此義也。成乃以立訓之,失其旨矣。所存於己者未定,補未定則擾矣。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暴人,謂衛君。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二〕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真者,矜名故也。智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 正外物篇:“德溢乎名,名溢乎暴。”是蕩即溢也。謂德洋溢於外,則德之名立焉,非謂喪真矜名也。凡相爭,則必用知,故知即為爭之兇器,不待橫出逾分也。成疏似覺過量。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按: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蘇輿云:“瘳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兇器。'”此淺言之,下複深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遊亂世而免於災,況懷兇器以往乎!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矼,愨實貌。”按:雖愨厚不用智,而未孚夫人之意氣;雖不爭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正氣,即下文“聽之以氣”之氣。下文“入則鳴,不入則止”,即能達人氣、達人心者也。否則,己之德雖厚,人之信雖實,且不爭善名令聞,然未通達人之氣與人之心,而強言自炫,殆難免災矣。此以信矼而強言,後以不信而厚言,兩層輕重,自是不同。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術同述。郭松燾云:“祭義:‘ 而術省之。'鄭注:‘術當作述。'”按:人若如此,則是自有其美,人必惡之。 正術,焦竑云:“江南古藏本作炫。”武按:孔子集語所引亦然。當作“炫”。前漢東方朔傳:“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師古注:“炫,行賣也。”又韻會:“自矜也。”惡,俞樾云:“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為文,當讀如本字。”俞說是也。言仁義,美德也,今強以此言炫鬻於暴人之前,是以人惡而無此美德,己則有之也。“ 其”字,指仁義繩墨言。有其美,即自炫也。命之曰災人。災人者,人必反災之,若殆為人災夫!成云:“命,名也。”釋文:“災音災。” 補災人,頂 “以人惡”來。以人為惡,是災害人也。若,汝也。“ 若殆為人災”句,應“若殆往而刑耳”。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衛君。”言汝唯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辯相鬥。 補釋文:“無詔,絕句。詔,告也。”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郭慶藩云:“熒,□之借字。說文:‘□,惑也。從目,熒省聲。'” 成云:“形,見也。”言汝目將為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救,容將益恭,心且舍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 盡。 補成云:“ 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擎、跽、曲拳,形跡斯見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諫。”按:此“若”字,訓如。 正前信矼強言,尚不免災,況不信厚言乎!較前進一步說。 “若”字當訓汝。此字領冒下句,而為二句主格也。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補再應“若殆往而刑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李云:“傴拊,謂憐愛之。”宣云:“人,謂君。” 補成云:“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割心。”釋文:“傴,紆甫反。拊音撫。”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名之心而陷之。一證。 補拂,釋文“符弗反,崔雲‘違也'”。擠,釋文 “子禮反,簡文云:‘排也。'一雲陷也。好,呼報反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三國名。 補釋文:“叢,才公反。有扈音戶,司馬云: ‘國名,在始平郡。'”按:即今京兆鄠縣也。奚侗云:“叢枝,齊物論作‘宗膾'。叢、宗音近。枝疑快字之誤,快、膾音近。”國為虛厲,宣云:“地為丘墟,人為厲鬼。” 正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武按: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禁令,物為之厲。”鄭注:“每物有蕃界也。”又春官:“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注:“ 厲,塋限遮列處。”句謂國為丘虛塋厲也。“國”字,總攝“虛厲”二字,宣乃以“國”攝“虛”,添一“人 ”字以攝“厲”,似與句意不合。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實,貪利。三國如此,故堯、禹攻滅之。 補影射衛君“輕用其國” 數句。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輿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為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恥為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 補此句雙承上二段,即以“名”字承龍、比,“實”字承三國,且作一小收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之實,雖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屈,況汝乎!正聖人,指龍、比、堯、禹言。龍、比不勝桀、紂之好名,致以身殉;堯、禹不能勝三國之求實,致以兵攻。不勝者,不能以德化而勝之也。此節引例以暢發“若殆往而刑”,與“必死於暴人之前”句。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謙虛。 補此“虛”字,緊貼“端”字,就容貌說,謂容貌端正而謙虛也,與後文“虛”字屬於氣與心者有別。若如郭注“正其形,虛其心”,則後文“虛者心齊” 之言便成贅疣。此句蓋回聆仲尼強言自炫,以下拂上之言,特欲以端虛自醫也。勉而一,黽勉而純一。 補此回聆仲尼雜多擾,及存己未定之言,特欲黽勉自存,求定於一,以免雜多擾之患也。此“一 ”字,系就以專一不雜之法,向人君進諫而言,與下“ 一若志”之一有別。蓋回此時,尚未領會仲尼“道不欲雜”之旨,誤以為進諫之法不欲雜,故以一自勉。及仲尼破其執而不化,即謂其執一也,回則張三法以應之,其不明仲尼之旨可知矣。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可,不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衛君陽剛之氣充滿於內,甚揚於外。 補成云:“充,滿也。孔,甚也。”武按:論語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 朱注:“血陰而氣陽。”淮南泛論訓:“積陽則飛。” 即陽充積向外飛揚也。本句跟上“其年壯”來,因衛君年壯,故陽氣方剛,積滿於內,甚揚於外也。采色不定,容外見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 補常人見衛君氣勢張揚,喜怒之色不定,故畏而不敢違忤。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規感動,乃因而挫抑之,以求放縱其心意。” 補應上“因其修以擠之”。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漬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進於大德乎!□補況驟然以仁義之大德強與之言乎! 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即相合,而內無自訟之心。”姚鼐云:“訾,量也。聞君子之言,外若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 正此與上句,宣注屬衛君說,姚同。武按:上明言衛君采色不定,按人之所感,以求快適其意,何能外合人之所言?且案者,即上文所謂擠也。方且案而罪之,豈僅內不自訟與不度量其義乎?宣、姚之說,均有未愜。應屬顏回說。訾,當從崔雲,毀也。仲尼對破回勉一之言,謂如執一不化,必至外合而內不敢訾。夫外合而內不訾,非內外勉而一者乎?且外合,即容且形之;內不訾,即心且成之也。況下文回明答“我內直而外曲”,外曲者,反應外合也;內直者,反應內不訾也。前後對勘,線路極為分明。其庸詎可乎!” 補此為對回之否定指示詞,益足證上語為對回說。如屬衛君,則此語為無謂矣。“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然則”下,顏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一無所求於人也。”補內直者,坦率任真,應訾則訾也。如童子率其天真而言,毫無蘄求之心,其善之與否,聽諸人而已。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純一無私,若嬰兒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宣云:“擎,執笏。跽,長跪。曲拳,鞠躬。” 補釋文:“擎,徐其驚反。跽,徐其裏反,說文云:‘長跪也。'拳音權。”人臣之禮也,補隨人跽、拳,盡人臣之禮而已,非外合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于古。” 正成人臣之直節,以謫過之言進,乃上比于古人,而與之為類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所陳之言,雖是古教,即有諷責之實也。 補釋文:“謫,直革反。”成云:“責也。”武按:“謫”字,反應上“不訾”。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三〕,雖直而不病,郭云:“寄直于古,無以病我。” 補“而不病”,明世德堂本、崇德書院本均作“不為病”,當從之。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補回見仲尼破其執一,乃張三條以救之。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釋文:“大音泰。”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所謂大多政也。”按:政、正同。法而不諜,俞云:“四字為句。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 諜,便僻也。'此‘諜'義同。言有法度,而不便僻。 ” 正此句當連上“大多政”為一句,言其大多正之之法而不諜也。“諜”字,俞引“形諜成光”句下釋文,訓便僻,不僅核之此處上下文義無當,即與“形諜成光 ”之義亦不合。武於彼句下,已加駁正,茲不贅。又釋文引崔云:“間諜。”武按:仲尼聖人,決無教弟子以間諜之法刺探人主意向之理,且與心虛之義亦未協。考前漢王莽傳云:“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注:“渫,徹也,通也。”“諜”“渫”二字,形近易誤。且諜,達協切,渫亦有達協切,音同則義通,故諜有通達義。彼以政令煩多而不渫,此以政法大多而不諜,意義正同。本篇要旨,在一“虛”字。虛以待物,則肆應無滯,達人氣,達人心,入則鳴,不入則止,胥此意也。回政法雖多,然拘之以三,仍不能圓通無礙,故曰“大多政法而不諜” ,謂其執而不能通達也。下句“固”字,亦即執而不通之謂。諜作如此解,則上下文義一貫矣。雖固,亦無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 正注非。前之“勉而一”,“執而不化”,固固矣;今法限以三,亦固也。雖固,其所言者,皆古人之所有,有類旁諷,不致直觸其怒,較前之強言自炫,與不信厚言者異矣,故不致招罪。雖然,止是耳矣,補耳,緩讀之則為而已,而已急讀之則為耳,故耳矣,即而已矣。此句言止於無罪而已。夫胡可以及化!不足化人〔四〕。猶師心者也。”成云:“師其有心。” 補師其成心,謂拘於三法而不諜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齋。” 補釋文:“齊,側皆反,下同。”武按:知北遊篇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此數句,足以發明此處“齊”字之義。有而為之,其易邪?郭云:“有其心而為之,誠未易也。” 正焦竑云:“張君房本‘有'下有心字。”武按:觀郭注亦應有。此句承上“ 師心”來。惟郭謂“誠未易也”,則與句意相違。徐鍇云:“人為為偽。”句意謂有心而為之,則非順乎自然之天,而純出於人為。人為即偽也。故曰“其易邪”,言易偽也。下文“易以偽”句,即承此而明說之。易之者,皞天不宜。”成云:“爾雅:‘夏曰皓天。'言其氣皓汗也。”按: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輿云:“易之者,仍師心也。失其初心,是謂違天。”於義亦通。 補釋文:“皞,徐胡老反。向云:‘皞天,自然也。'”武按:“皞”,一作“皓”,明也,白也。天地篇:“無為為之之謂天。”淮南原道訓云:“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也。”以此釋皞天之義最切。蓋本書所謂天者,無為也。無為者,不雜以人為也,即非有心而為之也。有心而為之者,人為也。人為者,易以偽,非純粹皓白之天所宜矣。回張三法,純出有心而為之,非任其自然無為之天而虛而待物也,故仲尼複申儆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為齊乎?”成云:“葷,辛菜。” 補釋文:“茹,徐音汝,食也。葷,徐許雲反。”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 “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雜也。” 補莊子之道,其功夫〔五〕即 在此,亦本篇主要語,即老子之“抱一 ”也。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欲致虛之極,在守靜之篤,欲守靜篤,則在抱一,即“一若志”之謂也。故一志為道家下手功夫,虛則其功效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成云:“耳根虛寂,凝神心符。” 補文子上德篇:“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注:“反聽內視。”武按:聽之以心者,即反聽也。與楞嚴經“初于聞中入流亡所”之義通。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聽止於耳,宣云:“止於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 正俞說非。如俞說作“耳止於聽”,謂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須知二句義同,徒滋重複,何申說之於有?且耳何能聽?能聽者耳根也。聲浪觸耳,耳亦不能止,能止者心也。上既言“無聽之以心”,即心寂然不動。聲浪之來,及耳而止,寂然之心不與之相應而為聽,故曰“聽止於耳”,與楞嚴經“ 聞所聞盡”之義相通。本文並未誤倒。心止于符。 俞云:“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于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 正俞說非。本書徐無鬼篇:“以心複心。”符、複義通。蓋人皆有心,或蔽而不明,或放而未收,遂有人心、道心之別,而不相符矣。如能一其志,使心不坐馳,物來順應,無差別心,無□緣心,無受、想、行、識之心數,二六時間,如如不動,則道心複而人心與之符矣。故曰“以心複心”也,故曰“心止于符”也。若以釋家言之,其入三摩提,證真如之境者乎?此就本書以證也。再以列子證之。仲尼篇:“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符者,合也。心止于符,即心止於合氣也。又本書則陽篇:“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本句所謂氣,即陰陽之氣也;本篇所謂道,即陰陽之公名也。列子曰:“天地之道,非陰則陽。”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莊子名陰陽之氣為道,即 本於此。是故心符於氣,即符於道,即所謂道心也。前後兩證,義自相通。此篇莊子寓諸仲尼之言,發揮修道次第,義最幽玄,語極精要,道笈丹經,汗牛充棟,悉不能出此範圍。審其修道次第,率由耳、眼兩根而入,與釋家相同,惟釋家入道方便,其途較多。然諸佛弟子,在祇桓精舍會上,應佛之問,陳述入道方便時,佛獨取觀音“由聞中入”,實以耳根圓通,遠較諸根為勝也。本篇先述耳根,眼根次之,其意與釋家亦無不同。其所謂“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者,即觀音聞所聞盡也;“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即覺所覺空也,覺屬心故也。氣充虛空,無乎不偏,圓之義也。心符於氣,即空覺極圓也。至列子所記亢倉子之言,尤有進焉。其言曰:“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即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也。又曰:“於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幹我者,我必知之。”此與觀音之“耳根圓通”何異?天地間祗此一理,孰謂釋道殊途乎?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申說氣。” 宣云:“氣無端,即虛也。”補即陰陽之氣。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虛者,心齊妙道也。” 補“虛” 字,為全篇主腦。應帝王篇云:“無為名屍,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於“虛”字之義,可謂發揮盡致。又管子內業篇云:“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又云:“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者,道乃可得。”文子十守篇:“虛無者,道之所居。”皆可作“ 唯道集虛”之參證。然道究何以必集於虛?其猶排橐乎?排橐內之氣,橐外之氣輒來補其空,如水之就下然。虛者空也。道為陰陽之氣,故集之也。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篇〔 六〕云:“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人既處陰陽氣之中,故心若虛,則是氣入而集之矣。所謂虛者心 齊也者,謂心何以虛?齊致之也。齊者其功,虛者其效也。說文:“齊,戒潔也。”禮記祭統云:“齊者不樂。 ”言不散其志也。不散志,即一志也。是則上文“一若志”,即示回以齊之下手處也。祭統又云:“ 定之之謂齊。”上文“存於己者未定”,即規回之未能齊也。達生篇:“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夫至忘四枝形體,則心可謂虛矣,亦即未始有回之義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使心齊之教。 正注非,說詳下句。實自回也;自見有回。 正奚侗曰:“自,系有字之誤。下文‘未始有回也 ',正與此文反應。”武按:此與上句,言回之未用其心也,實有一形體具備之回也。秋水篇:“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此即因其有而有之,任其天也。形質實有,不能故謂之無。如實有而以為無,非惟有心,且為妄心矣,何能致齊而虛其心?又何異釋家所斥墮於斷滅之外道乎?德充符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實自回也者,有人之形也;下文“未始有回也”者,無人之情也。尤為此處確證。此處就未用心時言齊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令,遂忘物我。 正“之”字,指心言。謂得使用其心時,未始有回之見存也。見不存,即任其天也。任天,即下文“為天使”也。此與大宗師篇“回坐忘”節可互相發明。夫功至坐忘,若准諸釋家,約等於斷煩惱、所知二障,而變人、法二空也。此就用心時言齊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成云:“ 心齊之妙盡矣。” 正“可謂虛乎”句,雙承上二意。謂未使心時,惟有人之形,既使心時,卻無人之情,如此者,可謂虛乎?二意夾詮,故夫子以盡虛之義許之也。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汝入衛,能遊其藩內,而無以虛名相感動。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則言,不入則姑止。 無門無毒,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楨云:“門、毒對文,毒及閘不同 類。說文:‘毒,厚也。言害人之草,往往而生。'義亦不合。毒蓋壔之借字。說文壔下云: ‘保也,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壔者,累土為台以傳信,即呂覽所謂“為高保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禱是壔之訛。壔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為保衛。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楨按:壔為毒本字,正及閘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按:宣說望文生義,不如李訓最合。門者,可以沿為行路;毒者,可以望為標的。“無門無毒”,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 正知北遊篇:“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此“毒”字,疑為“ 房”字之誤。此句為下句“一宅” 作根,並為後文“虛室”二字寫照。下句不得已而一宅之者,以其“無門無房”也。外無門,內無房,非虛室乎?以喻宅心于皇皇四達,內外無蔽障之所,斯可謂之虛矣。宣固望文生義,然李讀毒為壔,壔者,保衛之所,所以望遠通信者,非可常居,於下“一宅”與“虛室 ”義不相應,亦徒滋葛藤而已。至雲“使人無可窺尋指目”,則是偽也。若李林甫城府深阻者則如此,尤乖本文之義矣。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已而應之,非預謀也,則庶幾矣。” 補一宅者,宅居於一而不二也,為上“一若志”之喻。莊子之道,重在於不得已,故 “不得已”句全書數見,如下文“讬不得已以養中”,庚桑楚篇“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刻意篇“不得已而後起”。蓋即虛而待物之旨,必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也。下“葉公子高”節,即暢發此義,特提於此,以作彼節伏筆。絕跡易,無行地難。宣云:“人之處世,不行易,行而不著跡難。”正人行地而欲不留足跡,可以人為掃除之使絕,故曰易,以喻為人使,易以偽。又人無翼以飛,不能不行地,此天使之也。今欲無行地,非人為所能,故曰難,以喻為天使,難以偽。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欺;天然馭用,為而難矯。”補荀子性惡篇楊倞注:“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本書刻意篇:“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又曰:“動而以天行。”即為天使也。言循天理以行使,而不雜以知故之人為也。反之者,為人使也。為人使者,即使其知故,而流于人為之偽也。“為天使” 句,與上“寓於不得已”句相呼應。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釋文:“上音智,下如字。” 宣云:“以神運,以寂照。”正上知如字,音智非。無知不能知,猶之無翼不能飛,天使之也。無知欲知,無翼欲飛,皆難施以人為,故上言“為天使,難以偽”也。自“絕跡易”至此,皆推闡“入則鳴,不入則止”二句之義。蓋天者自然之謂,入則鳴者,順其自然之機也。如其不入,尚不知止而仍鳴,猶之無翼欲飛,無知欲知,皆違乎自然,而難於為力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司馬云:“闋,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境也。 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 補瞻,說文:“臨視也。” 成云:“觀照也。”闋,釋文“徐苦穴反”,集韻“音缺 ”。武按: 莊子於入道之門,上文示人由耳根,此處示人由眼根也。至天地篇所云:“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天聲之中,獨聞和焉。”則雙示眼、耳兩根,並說明其功效也。視乎冥冥,即瞻彼闋也;冥冥見曉,即虛室生白也,蓋說文訓曉為明也。又前漢書元後傳注:“曉,猶白也。 ”夫老、莊之道,多由眼根入。如道德經首章,即揭示觀妙觀徼,而繼之以觀複,終之以長生久視,從可知其入道之方矣。至虛室生白,並非甚難,如根性明利者,齊潔靜持,瞑目觀息,閱月經年,即見光透睫簾,白境現前矣。此境尚淺,因僅白生虛室,未能圓照十方也。准諸釋家,於四禪中,約等有覺、有觀之初禪乎?瞻闋 觀也;知白,覺也。靜瞻再進,則如庚桑楚篇之“宇泰定者發乎天光”,道德經之“明白四達 ”矣。更進則如在宥篇所述廣成子雲“吾與日月爭光” ,天地篇所雲“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夫形滅而惟乘光,即與光為一也,故謂上神。此與釋迦牟尼每于說法時,放種種寶光相若矣。此義請再以釋家明之。如阿那律陀云:“世尊示我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旋見循元,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又如周利槃特迦云:“我時觀息,微細窮盡。反息循空,其心豁然,得大無礙。”複如孫陀羅難陀云:“我初諦觀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身心內明,偏成虛淨,□相漸銷,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照十方界。”二家對勘,本文之義曉然矣。吉祥止止。成云:“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亦能致〔七〕善應也。”俞云:“‘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俶真訓:‘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列子天瑞篇盧重元注雲‘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按:下“ 止”字,或“之”之誤。 正惟道集虛,虛則吉祥自然來止,即下文“鬼神來舍”也。刻意篇云:“ 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澹然無極,虛也;眾美從之,吉祥止也。刻意篇又雲“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乃釋眾美之義也,亦可移以釋吉祥之義。又知北遊篇云:“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天和者,非吉祥乎?“止止”二字不誤,俞、王說均非。蓋止猶集也:上“止”字,吉祥來集也;下“止”字,心之所集也。心止于符,即心集於虛也,虛則吉祥來集。合而言之,即吉祥止於心之所止也。德充符篇“惟止能止眾止”,謂惟心之止,能止眾止也。若略變其句法,為“眾止止止”,謂眾止止於心之所止,義亦可通。淮南之作“也”字,因語氣已畢,用 “也”字以結之;此作“止”字者,為下句“止”字伏根。文義各有所當,何可據以改此乎?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神外 騖而不安息,是形坐而心馳也。 補此“止”字,承上句下“止”字來,謂心如不止,是形坐心馳也。可見上句下“止”字如作“也”字,則此“止”字無根矣。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於內;心智在內,而黜之於外。”成云:“虛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正徇,釋文“徐辭倫反。李雲‘使也'。”武按:此文亦為本篇要旨,且總結上文“無聽以耳”與“瞻彼闋”二節。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即徇耳內通也;瞻闋,即徇目內通也。文子上德篇:“夫道者,內視而自反。”舊注:“反應內視。”足證此義。“外”字,宣似作“內外”之外解,非是。前漢書霍光傳:“盡外我家。”師古注:“外,疏斥之。”外於心知者,謂黜心知而不用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品物之本也。”說文:“鬼,陰氣。”是靈即鬼也。陰陽之氣曰道,陰陽之精曰神鬼。是則鬼神來舍,與上“惟道集虛 ”相應。管子心術篇:“虛其心,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內業篇:“敬除其舍,精將自來。” 本書知北遊篇:“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凡此,皆可為此處參證。且此節之義,與釋家之旨亦相通。如楞嚴經云:“於外六塵,不多流逸,旋元自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玩“反流 ”以上各語,即徇耳目內通也。全一者,即一若志也。六用不行者,眼、耳、鼻、舌、身、意不行也。此所謂心知,即彼所謂意也。外於心知,即意不行也。彼言六塵六用,舉其全也;此僅言耳、目、心者,從其重者言之也。內懸明月,則虛室生白之謂矣。措辭雖殊,義則無二。釋道異同之爭,亦徒見其淺陋而已。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幾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物之綱紐,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幾散之人,有不為所化乎!成云:“幾蘧,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君。”蘇輿云:“言知此可為帝王,可以宰世,而況 為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補釋文:“紐,徐女酒反。崔云:‘系而行之曰紐。'”武按:此“化”字,總結上文二“化”字。伏羲、幾蘧之行終,言伏、幾之行,終盡於此道也,反結上文“非所以盡行也”句。
〔一〕“笑”字,據集釋引成疏補。
〔二〕“乎”原作“者”,據王氏原刻及集釋本改。
〔三〕“者”字,據王氏原刻及集釋本補。
〔四〕“人”原作“也”,據王氏原刻改。
〔五〕“夫”原誤“大”,據文義改。
〔六〕“如天之為”原作“天地陰陽 ”,據春秋繁露改。
〔七〕“致”字,據王氏原刻及成疏補。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 委寄甚重。” 補釋文:“葉音攝。子高,楚大夫,為葉縣尹,僭稱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緩于應事。” 正不急,言齊侯不視之為急務也。不視為急務,則必不重視使者矣。此對照上“ 重”字說。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栗之。懼也。 補釋文:“栗音栗。”武按:未可動,未可以言動也。使者責在傳言,葉懼不能傳達其言,且無以對楚王使之甚重也。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無大小,鮮不由道而以歡然成遂者。 正郭云:“夫事無大無小,少有不言以成為歡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者也。”玩郭注,是以“言”釋“道”字,是也。觀後文“丘請複以所聞”云云,仍從“言”字立論。所謂複者,前所告者,資言以成歡,此複以傳言各義相告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降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二氣將受傷而疾作。” 補淮南原道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本書在宥篇:“ 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武按:懼與怒同屬陰,當事未成,則懼,事成則喜。懼則破陰,喜則墜陽,故有陰陽之患也。墜陽則陰勝,必致寒疾,破陰則陽勝,必致暑疾,即所謂寒暑之和不成也。葉慮事不成而懼,陰破陽勝而致暑疾,所以內熱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于前塗,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 ”以上述子言。蘇輿云:“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為能。”按:成說頗似張浚符 離之敗,未可為訓。蘇說是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云:“甘守粗糲,不求精善。” 補釋文:“臧,作郎反,善也。”爨無欲清之人。 成云:“清,涼也。然火不多,無熱可避。” 補釋文:“爨,七亂反。清,七性反。字宜從冫,從□者,假借也。”武按:呂氏春秋功名篇:“大熱在上,民清是走。”亦作“清”。列子楊朱篇:“薦以梁肉蘭橘,心□體煩,內熱生病矣。”據此,則內熱之來,由於肥膿美食。治此美食,用火必多,則爨者必思就清。今爨無欲清之人,食粗薄而無須多火也。食既粗薄,則內熱不由此致矣。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憂灼之故。 補內熱既非由於美食,則由甚栗之故也。蓋甚栗破陰而陽勝,必致暑疾。左傳昭西元年秦醫和曰:“陽淫熱疾。”外物篇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同此義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行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雲“戒,法也。”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受之于天,自然固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不論境地何若,惟求安適其親。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險,安之若命。”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 施讀〔一〕為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荀子儒效篇‘哀虛之相易也',漢書衛綰傳‘ 人之所施易',義皆同。正言之則為易施,倒言之則為施易也。”宣云:“事心如事君父之無所擇,雖哀樂之境不同,而不為移易於其前。” 補釋文:“施,如 字。崔以豉反,移也。”武按:注中“ 哀”當為“充”,“易”上脫“施”字。考儒效篇:“ 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充,實也。施讀曰移。”此段事親、事君、事心,三者平舉。因葉言為人臣者不足以任,故以事君之道語之,事親數語,特文之陪襯耳,然尤重在事心。下文皆就事心之義發揮,蓋針對葉之甚栗內熱,由於不能事心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情,實也。補此二句為本節要語。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即下文“讬不得已以養中”也。安命即所以養中也,亦即前節之齊也,均就事心言也。心能安而養之,哀樂自不易施乎前,而心虛矣。如此,則羲、蘧之所行終,故曰“德之至也 ”。上下兩節,義自相通。且不特此也,如德充符篇“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達生篇“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其義亦相通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尚何陰陽之患?” 補安之若命而已。夫子其行可矣!補上節回師心外馳,自來請行,仲尼以“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規之,以其未可行也。此節子高心栗內熱,謂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自不欲行也,仲尼以“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以曉之,勉其行也。兩節對照,一反一正,同用兩“何暇”句以相關顧。想莊子著筆時,亦煞費排比結構之功也。丘請複以所聞:更以前聞告之。凡交,交鄰。近則必〔二〕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順以信行。” 補靡,御覽四0六引作“磨”。郭云:“ 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與宣注同以順訓靡,是也。遠則必忠之以言,宣云:“相孚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宣云:“必讬使傳。”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 之言,常過其當。”凡溢之類妄,成云:“ 類,似也。似使人妄構。” 正類,比也。凡過當之言,離於常情,故比類於妄也。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致疑貌。” 正奚侗曰:“論語:‘無莫也。'邢疏:‘莫,薄也。'信之也莫,猶言信之不篤也。”莫則傳言者殃。補此其所以為天下之難者也。應上文“人道之患”。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法言名因此。‘ 傳其常情,宣云:“但傳其平實者。” 無傳其溢言,郭云:“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按:引法言畢。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按:鬥力屬陽,求勝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 補成云:“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戲之情在喜,終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武按:此喻溢惡。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治,既醉則終於迷亂,昏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 補成云:“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云云。武按:此喻溢美。此兩喻,皆下文陪襯,亦即下文之喻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宣云:“諒,信。鄙,詐。”俞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為都。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而為諒,遂失其恉矣。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誌。” 正俞說非。俞謂 “諒與鄙,文不相對”。夫諒,信也;鄙,詐也。一正一反,俞據何文例,謂不相對?尹文子大道篇“能鄙不相遺,賢愚不相棄”,能鄙、賢愚,皆一正一反相對。淮南本經訓“仁鄙不齊”,仁與諒為同類。鄙可與仁對舉,獨不可與諒相對乎?又禮記樂記:“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此就樂之正面言也。其反面則曰:“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則正以諒與鄙相對也。至引淮南以證此文“鄙”應 為“都” ,不知淮南就軍亂言,謂軍亂始都城,常大於鄉鄙,以鄙較都地廣人多,亂易擴大也。各有取義,何可引以證此?俞亦自知“大”字未安,則又謂為誤,而引此“卒 ”字以正之。易“卒”於彼,彼文不安矣;易“都”於此,此文不安矣。蓋此文系寫傳言者貴信而不可妄,“ 諒”承上文“信”字,“鄙”承上文“妄”字,脈絡分明。如易“諒”為“都”,則“鄙”變為“ 邊鄙”之鄙,此二句變成贅疣,與上文全無干涉矣。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如風之來,如波之起。 補“其作始”二句,承上啟下。夫言或溢美,或溢惡,如風波不定也。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者,縱而舍之。實喪,猶得失也。” 正郭說非。夫溢美、溢惡如風波之言,其言類妄,妄則非實矣。如使者遵行而傳之,非喪其實乎?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曰“易以危”。正妄則傳言者殃。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中之故。 補巧言始乎陽也,忿設卒乎陰也。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獸困而就死,鳴不擇音,而忿氣有餘。于其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 補釋文:“茀,郭敷末反,李音怫。”武按:此喻陰陽之患。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克求精核太過,則人以不肖之心起而相應,不知其然而然。 補克核大至,言遇事考慮成敗太過,則患得患失之心應之,即不肖之心應之也。此屬一己說,針對葉公過於患事之成不成而發,于本文義似較聯貫。又克核大至,過乎諒也;不肖之心應之,卒乎鄙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宣云:“必罹禍。”故法言曰:‘無遷令,成云:“君命實傳,無得遷改。”無勸成。'成云:“弗勞勸獎,強令成就。”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是增益言語。 補上文“溢美”“溢惡”,乃君因一時喜怒致言之溢也。此之過度, 則傳言者過乎君言之限度也。遷令、勸成,即皆過度也。遷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 補上文“妄則傳言者殃”,及“實喪易以危”,就危及使者之身言之也。此之遷令、勸成,則妨害所使之事矣。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成而惡,必有不及改者。 補此對上葉公“若成若不成” 之問而答之也。言事之美成者,非倉猝可致,必須多經時日;如為惡成,後雖悔改,勢已不及矣。本書徐無鬼篇:“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緣功,其果也待久。”“殆之成也”句,即惡成不及改也。“其果”句,即美成在久也。可以互證。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讬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讬于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補乘物以遊心,則心不至克核矣。讬不得已以養中,與上文“寓於不得已”,及“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同義。何作為報也!郭云:“任齊〔三〕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 補報者,謂齊對楚報答之言也。子高見齊之甚敬而不急,慮其所報不足以厭楚王之意,則己必得罪,故甚栗之。是即作意于齊之報也。仲尼針對其病,故以“遊心”“養中”二語勉之。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為難。若人道之患,非患也。 正成云: “直致率情,任於天命,甚是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武按:上言“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又言“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今勉以讬不得已以養中,於身且忘,況傳常情,不傳溢言,但直致君之命耶!此豈有難者,收繳上“難” 字。
〔一〕“讀”原作“謂”,據集釋引改。
〔二〕“必”字,據王氏原刻及集釋本補。
〔三〕“齊”原作“其”,據王氏原刻及郭注改。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釋文:“ 顏闔,魯賢人。太子,蒯聵。”而問于蘧伯玉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嗜殺。 補釋文:“ 蘧,其居反。伯玉,名瑗,衛大夫。”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宣云:“縱其敗度,必覆邦家。” 補方,道也,法也。 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先將害己。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己過。 補足以知人之過而責之,而不知人之所以有過而原之。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補此句重要,統攝下文。下文形。身之外見者也;心,身之內在者也。就不入,和不出,即正身之謂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示親附之形,內寓和順之意。” 正此二句,說明正身之義也。形莫如就,謂身日與親近而順應之。下文“與之為嬰兒”數句,即就之說也。宣以順訓和,與下文意不合。蓋心如順之,則入而與之同矣,豈非與之為無方而危國乎?郭雲“和而不同”,義為近之。然本書山木篇云:“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上下以和為量,即不上不下而處中也。中庸雲“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義亦猶此。文子上仁篇“和者陰陽調”,即陰陽不偏勝而為和也。淮南泛論訓:“陰陽相接,乃能成和。 ”謂陰陽相沖和也。廣韻:“和,不堅不柔也。”均有不偏不倚,而歸於中正之義。蓋職傅太子,位居親近,其勢自不能與之疏遠,故曰“形莫若就”也。然既不可與之同而危國,又不可與之迕而危身,二者之間,惟有不上不下,不堅不柔,調喜怒之陰陽,允執厥中而已,故曰“心莫若和”也。知北遊篇:“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此文亦言“正汝身”,正身者,乃所以致和也。“心和”二字,為本節主腦,亦本篇要旨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宣云:“猶未盡善。 ” 正宣注非。上祗言就與和,何得謂未盡善?此雲“ 有患”者,患在下文入與出也。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附不欲深,必防其縱;順不欲顯,必範其趨。 正郭云:“入者遂與同,出者自顯伐也。 ”武按:就者,不過身與之近;入則同流,必致心亦附 之,則損和矣。出者,表而出之也。下文“積伐而美者”,即出義也,出則非和矣。又上文“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炫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亦可證“ 出”字之義。達生篇:“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柴立中央者,處和也,足與此義相發。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顛,墜。滅,絕。崩,壞。蹶,僕也。 補其德天殺,勢必傾危,入而與同,亦必同難,故為顛、滅、崩、蹶也。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且惡其勝己,妄生妖孽。” 正心和而出者,積伐而美也,即露才揚己也,故為聲為名。人君因案人之所感,且因其修以擠之,則為妖為孽矣。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喻無知識。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無界限。喻小有逾越。補釋文:“町,徒頂反。畦,戶圭反。李云:‘町畦,畔埒也。'”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不立崖岸。 補自“嬰兒 ”句至此,其義與應帝王篇“虛而委蛇,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同。達之,入於無疵。順其意而通之,以入於無疵病。 補釋文:“疵,似移反,病也。”句謂因勢而利導之,以入於無疵。此為日漸之德有成也。上“嬰兒”數句,就之實也,此則和之效也。如入或出,則不能致此矣。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伐汝之美,以犯太子,近似螳蜋矣。一喻。 正“螳蜋”句,亦見天地篇。又淮南人間訓云:“齊莊王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禦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蜋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回車而避之。”韓詩外傳同。成云:“螳蜋,有斧蟲也。”武按:螳蜋怒臂,莊公回車,其才實勇,故曰“是其才之美者也”。積伐者,屢屢誇稱也。積伐而美者以犯之,與上“強以仁義繩墨之言炫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有其美也”同義。謂屢以仁義之美,進言于太子,無異屢誇己有此美,而欲太子效之也。如此以犯太子,必致觸忌,而與螳蜋當車之所為相近矣,故曰“幾”也。或云:“伐”字,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小爾雅:“伐,美也。”幾,易系辭:“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猶雲端兆也。而,應如字讀。積伐而美以犯之幾者,謂積累功伐而才美者,即為犯人主猜怒之端。蓋妒才忌功,暴君通性,良弓走狗之禍,空梁燕泥之誅,于古數見,豈緣誇伐!即上文龍、比之死,因修見擠,亦非由誇也。此足備一說,然究不若前說之當。 “螳蜋”至此,為心和而出作喻。“積伐而美”二句,為下“匠石”數節之反面張本,“山木”“膏火”一段之正面張本。換言之,以下各節,即為此二句之正喻反喻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先為分決,不使用力。” 正此為“嬰兒”數句作喻,即為“就”字作喻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不可怒之。再喻。 補自“養虎”句至此,達之入於無疵也。虎性殺人,逢其怒也。達其怒心,則媚養己者,而無殺人之疵矣。以喻太子,其德天殺,殺由於怒也。達其怒心,則無殺人之疵矣。能達其怒心者,就與和致之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成云:“蜄,大蛤也。”愛馬之至者。 補釋文:“盛音成。矢或作屎。蜄,徐市軫反。溺,奴吊反。”郭云:“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者也。”適有□虻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言□虻附緣于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補釋文:“□音文。本或作□,同。虻,孟庚反。僕,普木反。”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時,掩馬不意。” 正注非。不時者,時而拊,時而忘拊也。忘拊之時,則馬不耐蚊虻之虐,而缺銜脫奔,必致毀傷途人矣。考成原疏云:“蚊虻 群聚緣馬,卒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人遭蹄蹋也。”成意如定時拊,則馬不驚。不知蚊虻之來緣也無時,拊之又何能確定時節?拊者,拂去蚊虻而已,著必不重,馬何至驚駭傷人?嘗見牧童猝鞭其馬矣,未見其驚傷如此也。如遇毒蚊群緣囋螫,而不為之拊,則真缺銜絕轡,狂奔傷人矣。則缺銜、毀首、碎胸。成云:“銜,勒也。”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為馬除蚊虻,意有偏至,反以愛馬之故,而致亡失,故當慎也。三喻。 正王解本于郭、成。考郭釋“意”字,謂在於拊蚊,成釋“亡”字,謂失其所愛之馬,均非也。文之本義,謂器盛矢溺,愛馬之意有所至矣。然蚊虻僕緣,馬切身之患也。愛馬者,尤當隨時拊之。今不時拊,則其愛有所遺亡矣。此段為形就而入作喻。謂入與之同,乃求合人主,免犯其怒也。然偶失其意,即足致患。如愛馬者,可謂至矣,偶一忘拊,即致毀碎。推之應世,亦複良難,要當慎之而已。“ 慎”字,總收上二“慎”字。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道。”成云: “如轘轅之道也。社,土神。櫟樹,社木。”補藝文類聚八九、御覽九五八引“轅”作“園”。釋文:“崔云:‘道名'。”武按:總之地名也。司馬、成氏,未免臆說。釋文:“櫟,力狄反,李雲‘木名',一雲‘梂也'。”社,成云:“土神也。”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注:“大夫以下,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裏社是也。”周官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按此櫟社,蓋如周官說,以木名也。其大蔽數千牛,潔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潔,匝也。”李云:“徑尺為圍,蓋十丈。” 正釋文:“蔽牛,必世反。李云:‘牛住其旁而不見。'潔,向、徐戶結反。”武按:如李說,圍十丈,安能蔽數千牛?“ 求高名之麗” 句下,引崔雲“環八尺為一圍”,方與蔽牛義不戾。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俞云: “旁、方古通。方,且也。言可為舟者且十數。” 正釋文:“七尺曰仞。或云:八尺曰仞。”武按:旁,崔雲“旁枝”,是也。俞說非。此“旁”字,跟上句“枝 ”字來。上文蔽千牛,潔百圍,形容正幹之大也。可為舟者十數,言其旁可刳為舟之枝以十數。此形容旁枝之大且多也。枝大,益顯幹大矣。此莊子行文之妙,且密而有法也。古者刳木為舟,旁枝之大者,斷而刳其內,即可成舟,如大幹,則不易如此刳用矣。俞乃不從其易而從其難。觀其原文,徵引多書,以證“旁”之為“方 ”,方有數義,又必限之為且。如此作注,亦太費周折矣。即依俞說,而以修詞之例審之。此段連用三“其” 字,為句中主格,均指幹言。如旁訓且,則“為舟”句系頂幹說,仍形容幹之大矣,不與上蔽牛之形容相複乎?況方義如儀禮大射禮“左右曰方”注:“方,旁出也。”據此,則照本字讀,固為旁枝;讀作方,亦旁出之枝也。俞原文尚有云:“在宥篇‘出入無旁',即出入無方。此本書假旁為方之證。”此說更非。所謂假者,本無此字,假他字以寓此字之義也。在宥篇“出入無旁 ”之上,即有“行乎無方”之“方”字,更何須假“旁 ”?如硬派為假,未免冤苦莊子。至出入無旁,應讀為 “依傍”之傍,謂塊然獨立,出入無所依傍也。如訓為方,于上文“行乎無方”犯複矣。且行可無方,既有出入,出入即其方也,何能雲無?總之,無一而可也。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遂,竟也。文選注引司馬云:“匠石,字伯。”弟子厭觀之,厭,飽也。走及匠石,曰: “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補釋文:“輟,丁劣反。”成云:“止也。”斤,正字通“以鐵為之,曲木為柄,剞劂之總稱”。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體重。以為棺槨則速腐,多敗。以為器則速毀,疏脆。以為門戶則液樠, 李楨 云:“廣韻:‘樠,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樠正取此義。” 正釋文:“樠,郭武半反。”武按:李楨原文“ 正取此義”下,尚有“謂脂出如松心也”句,于義方合。王遺此句,則為為門戶者,別屬液樠木,而非櫟矣。 以為柱則蠹。蟲蝕。 補蠹,釋文“丁故反”。成云:“木內蟲也。”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已見逍遙游諸篇。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可成章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成云:“ 蓏,瓜瓠之類。” 補釋文:“柤,側加反。蓏,徐力果反。”成云:“在樹曰果,柤、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集韻:“柤,詐平聲。”廣韻:“同樝,似梨而酸。”柚,集韻“餘救切,音右”。說文與“□”同,“條也”。書禹貢:“厥包橘柚。”傳:“大曰橘,小曰柚。”爾雅釋木:“柚,條。”注:“似橙而酢。”列子仲尼篇張湛注:“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武按:書傳謂“小曰柚”,誤也。淮南主術訓:“夏取果蓏。”高注:“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漢書食貨志: “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為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 楊注:‘ 抴,牽引也。'小枝抴,謂見牽引也。” 正泄,釋文:“徐思列反。崔云:‘泄、泄同。'”成云:“大枝損,小枝發洩。”武按:果累累者,必大枝也,故人每攀折之以剝果。小枝生氣,輒從大枝折處泄出,而易萎矣。故工於移植果樹者,一遇大枝剪折處,必用泥封,以免泄其生氣,則植之易於成長。此文正合此理。俞乃謂“泄字之義,於此無取”,改讀為抴。武以為于古人之書,照本字詁之,即或義未盡協,較之專輒改字改音者為妥。清之訓詁家,類蹈擅改之病,非武所敢苟同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掊擊由其自取。成云:“掊,打。” 補“柤梨”至此,申說上節才美犯幾之義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幾伐而死。 補成云:“幾,近也。”武按:“無所可用”者,謂無可得而用之也。櫟雖無用,特不可用為器耳,仍有用為薪之慮,故久欲求一無所可用之地以自全。幾死者,因人覬覦欲得為薪也。乃今得之,郭云:“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 正社樹人民所尊,雖為有用,猶不翦伐,況無用者乎!乃今得為社,翦伐可免,故謂“為予大用”也。為予大用。成云:“方得全身,為我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幾,近也。 補汝以我無用,而謂之為散木,則必自以為有用,而非散人矣。不知有能者苦其生,有用者幾於死,汝幾死之人也,亦何莫非散人乎?散人又何足以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云:“診讀為畛。爾雅:‘ 畛,告也。'告其夢于弟子。”正王說非。本書非無“畛”字,如齊物論“請言其畛”是也,此如應為畛者,莊子何以不用,而必用診,以勞後人揣測改讀乎?莊子恐不如是之傎也。王氏原文云:“ 向秀、司馬彪並云:‘診,占夢也。'按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櫟社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為畛。”云云。武按:王氏之意,診既訓為占,占則必有端策拂龜之事,此意無乃太固?爾雅釋言:“隱,占也。”疏:“視兆以知吉凶也。必先隱度,故曰:隱,占。”然則匠石亦必以夢與弟子相與隱度之,故下有“密,若無言”之語也。此與占義合,即與診義合也。又前漢書陳遵傳: “馮幾口占書數百封。”然則“診”之雲者,匠石對其弟子口占耳。此義尤切,何勞繳繞傅會,擅改為“畛” 乎?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既急取無用以全身,何必為社木以自榮?正玩注,訓趣為急,于文意不合。成雲“櫟木意趣,取於無用”,是也。文謂社之義在保民,為社即須盡保民之用,既旨趣在於無用,則為社是何意乎?注謂“以自榮”,于文無據。曰:“密!”猶言秘之。姚鼐云:“密、默字通。田子方篇仲尼 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 正 “密”“默”二字,涵義各別。默,緘默不言也;密,隱秘勿泄也。此“密”下接“ 若無言”,戒其無以以下諸語外泄也。其戒密之意,一以儆於夢責,恐複為櫟所聞;二以社為眾所祈福讬保之處,泄則恐眾知其無保民之用而來紛議。故此處以“密”字為當。至仲尼語顏以“默”,其義稍別。謂文王盛德,無容言議,故下即接以“又何論刺焉”之句,非有宣洩之慮也。故以“默”字為當。達生篇之“密”,乃魯公恐顏闔料敗之言宣聞於東野,必調緩其馬,或不致敗,即無以驗顏闔之言,故公密而不應也。以此見二字之未可隨意通用,且見莊子下字之精審也。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聽不知己者詬病之而不辭也。司馬云:“厲,病也。” 補彼亦直寄焉者,謂彼非為社也,特寄於社而為社木而已。上“散木也”至“不材之木”數句,即詬厲之語也。“不知己” 三字,跟上“又惡知散木”句來。文謂彼之無用,乃大用也,人反以無用詬之,即不知己者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如不為社木,且幾有翦伐之者,謂或析為薪木。正為社與為社木,其義各別,注於此尚未認清。上直寄焉者,為社木也。而社之義在保民,遵社之義而盡保民之用,則為社也。列子周穆王篇:“幾虛語哉!”注:“幾音豈。”此謂即不為社義而施保民之用,然既寄為社木,民豈有翦伐者乎?以社雖無靈,人民必不致翦伐社木也。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保于山野,究與俗眾異,非城狐、社鼠之比。 正眾,指眾社木。言彼無為社保民之用,特寄於社,期乎自保,以免翦伐,非若眾社木之義在保民也,故曰“所保與眾異”。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宣云:“義,常理。”按:彼非讬社神以自榮,而以常理稱之,於情事遠也。 正謂以尋常保民之社義譽之,不亦遠於事實乎!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司馬云:“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向 云:“藾,蔭也。”崔云:“隱,傷於熱也。”成云:“駟馬曰乘。言連結千乘,熱時可庇於其蔭。” 補釋文:“乘,繩證反。芘,本亦作庇。藾音賴。”武按:“隱”字,玩注意屬下句,似應屬上句。崔訓傷熱,不知何據,恐系臆說。說文云:“隱,蔽也。”國語齊語“隱五刃”,注“藏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避也”。“其”字指大木,謂如有結駟千乘,避藏於其下,將可受芘於大木之所蔭也。此系借千駟之隱,以譬其蔭之廣,觀“將”字可知,固不必限於傷熱時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言必可為材也。 補此“異”字,照應上“異”字。上言其形之異,此因其形異,而揣其材之亦必異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樑;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成云:“軸,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按: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綴。 補“見”,明世德堂本作“視”,應從之。蓋見無心,視有意。句冠“ 俯”字,即俯身視察之也。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 李云:“狂如酲也。病酒曰酲。” 補釋文:“咶,食紙反。酲音呈。”武按:“咶”與田子方篇“舐筆和墨”之“舐”,釋文同音食紙反,故二字通。又按藝文類聚八八引“口”作“舌”,應從之。因咶葉者舌,應舌爛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為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斧斤〔一〕,而庇蔭千乘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由木悟人。宣云:“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 補此與上段,皆言不材之木,明無用之旨,於義似複,而有不復者在。匠伯,攻木之工也,其於櫟,遙望即知,過前不顧;南伯則仰視俯察,舌咶鼻嗅,方知不材。不復者一。後木,枝拳根解,葉爛口而嗅致狂;櫟必無是,故觀者如市,而弟子屬厭。是知不材之度,後深於前。不復者 二。櫟非盡無用,而求無所可用,故寄社以自保;後木則不須如是也。不復者三。櫟似材而實非材,其沈腐液蠹之性,存於內而驗於後,非稔知木性者不辨,故用攻木之匠伯;後木拳解形於外,爛狂效於前,一經察試,即知不材,衡厥無用,無殊槁木,故用形如槁木之南伯。不復者四。以此知莊子所引故事,所用古人,非由率爾,咸寓深意,顧尚雲複乎?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 荊氏,地名。”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宣云:“杙,系橛也。 ” 補成云:“狙猴,獮猴也。”釋文:“狙,七餘反。杙,以職反。”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崔云:“環八尺為一圍。”郭慶藩云: “名,大也。”(詳天下“名山三百”下。)成云:“ 麗,屋棟也。”補秋水篇:“梁麗可以沖城。”列子湯問篇:“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麗,三日不絕。”據此,則麗、梁、棟,一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斬之。釋文:“椫,本一作擅。”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椫傍。其木極大,當斬取大板。”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二〕,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三〕者,不可以適河。郭云:“解,巫祝解除也。成云:“顙,額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正前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師古注:“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又淮南修務訓:“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于陽盱之河。”張湛注:“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 ‘解除'之解。”然則古是有用人求解於河之事,特未必真沈人於河耳。如禹以身解於河,但以為質,並未沈身。修務訓又雲“湯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亦不過斷發剪爪,權充犧 牲,亦未以身殉之也。鄴中沈人祭河,偶遇凶巫蠱惑,系一地一時之事,未可引以例常。如鄫子用人于次睢之社,距可謂春秋時凡祭社者必用人乎?又如御覽一○引莊子佚文云: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蔔云:‘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如其時人祠已成習,景公何至不從?亦系卜者一時之誣妄而已。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 補楚語下篇:“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注:“覡,見鬼者也。”周禮男亦曰巫。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宣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
〔一〕“斧斤”,原作“斤斧”,據王氏原刻及莊子原文乙正。
〔二〕“斧斤”,原作“斤斧”,據王氏原刻及集釋本乙正。
〔三〕“痔病”,原作“痔瘡”,據王氏原刻及集釋本改。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 補廣韻五支下云:“漢複姓。莊子有支離意,善屠龍。”則此支離,乃疏之姓也。然莊多寓言,人名每寓妙旨,故下有“支離其形”之誤,司馬注亦未為非也。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頭縮也。”淮南曰:“脊管高於頂也。 ”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崔云: “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說是。大宗師篇‘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如贅。'亦與崔說證合。素問剌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彤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 骨會大杼。'張注:‘ 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檠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大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玉篇:‘□,木□節也。'與脊節正相似。從木作□,於義為長。” 正釋文:“會,徐古活反,向音活。撮,子活反。”武按:朱桂曜云:“向音活,活疑括誤。”朱說是。因集韻等書,括亦古活切也。崔雲“會撮,項椎”,不知何據。凡言骨節者,無過素問、靈樞二書,並無骨名會撮者。李楨僅憑難經中一“ 會”字,即謂“會撮從此取義”,殊為武斷。考儀禮士喪禮“鬙用組”,鄭注:“用組,組束發也。古文鬙皆為括。”又詩 車轄“德音來括” ,傳:“括,會也。”可證“鬙”“會”“括”三字通用。詩小雅:“ 台笠緇撮。”疏:“小撮持其發而已。”故會撮即束會而撮持其發也。寓言篇:“向也括,今也披發。”“括”字亦就發言。且張君房本“括” 下有“撮”字,益足證司馬之說是,而崔、李之說非也。五管在上,李云:“管,腧也。五藏之腧,並在人背。”李楨云:“頤、肩屬外說,會撮、五管屬內說。”正會撮為髻,亦屬外說。兩髀為脅。司馬云:“脊曲髀豎,故與脅肋相並。”挫針治繲,足以糊口;司馬云:“挫針,縫衣也。繲,浣衣也。”正釋文:“挫,徐子臥反,崔雲‘按也'。繲,佳賣反。糊,徐音胡,李雲‘食也。'”成云:“糊,飼也。”武按:楚辭招魂:“挫糟凍飲,酎清涼些。”注:“ 捉去其糟,但取清醇也。”是訓挫為捉也。集韻:“繲,居隘切,音懈,故衣也。”據此,則挫針治繲者,謂捉針縫治故衣也,全句祇說一事。若如司馬說,分為縫、浣二事,必非有常疾之支離所能兼任。即今市廛業縫補與浣濯者,亦尚分工而無兼者,可以推知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簸也。小箕曰筴。簡米曰精。”成云:“ 播,揚土。” 正注非。釋文:“筴,初革反。崔云: ‘鼓筴,揲蓍鑽龜也。鼓筴播精,言賣蔔。'”武按:崔說得之。曲禮“龜為蔔,筴為筮”,儀禮士冠禮“筮人執筴”,楚辭“詹尹乃端筴拂龜”,足證鼓筴即揲蓍也。蔔筮之道,有□筴、揲筴、分筴、扐筴等事,句中 “鼓”字,足以該之。管子小匡篇:“握粟而筮者屢中。”握粟,猶之播精也。王應麟曰:“‘播精',文選東方朔畫贊作‘播糈'。”考畫贊為夏侯湛撰,其序云:“支離覆逆之數。”注:“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糈,足以食十人。'糈音所。”又史記日者列傳:“夫蔔而有不審,不見奪糈。”集解:“離騷經云:‘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 索隱:“糈者,蔔求神之米也。言蔔之不中,不見奪其糈米。”據以上各說,可見古之買蔔者,必出糈以享神,蔔後,無論中否,糈歸蔔者。就享神言,謂之糈;就蔔者言,謂之精。猶之享神之牛謂之犧。糈與精,一也。支離賣蔔得糈,故足以食十人,如 為人簸揚精米,恐尚不敵治繲之糊口,惡能食十人乎?且試涉足鄉曲,從事箕簸者,所在可見,其人必仰項伸腰,以相揚扇,試問傴僂如支離者能為之乎?故鼓筴播精為蔔筮,不待煩言而解矣。上征武士,則支離攘臂而游於其間;郭云:“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 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司馬云:“六斛四鬥曰鐘。”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猶如何。 ” 補成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武按:接輿,又見逍遙遊篇“吾聞言於接輿”句下之注。蓋楚之賢人,見人世危殆,讬於狂以自隱者也。見孔子周流各國,志在用世,故遊門作歌以諷之。史記孔子世家:“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因以至楚,在魯哀公四年。六年,自楚反乎衛。接輿作歌,即其時也。 正如,往也。德,指當世說,合下“來世”“往世”為三世。文言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當世則德衰,鳳兮鳳兮,欲何往乎?下“趨”字,即應此“往”字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輿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苟生當有道,固樂用世,不僅自全其生矣。”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宣云:“全其生。”補此段言天下有道,惟望諸來世,見諸往世耳。然來世未至,胡可久待?往世已逝,渺難追尋。今值無道之世,惟有全生而已。必如此解,上“來世”二句方不落空。天地篇云:“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足明此與上二句之義。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補方今天下無道,僅免刑而生也。找足上“生焉”句。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不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不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 補天下有道,則仕而成其功;天下無道,則隱而全其生。行隨世變,不拘一隅,即在宥篇所謂“大人行乎無方”者也。孔子則不顧世亂身危,棲遑求用,猶之指畫一定之地,以自限其趨,必致跬步難行,惟有危殆而已。迷陽迷陽, 謂棘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楚輿夫遇之,猶呼“迷陽踢”也。迷音讀如麻。 正吾亦楚人,未嘗聞“迷陽踢”之名,遍詢輿夫,亦無知者。當是王聞未審,不足據也。其曰“棘刺”者,蓋有所本。詩召南草蟲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朱注:“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羅勉道云: “迷陽,蕨也。”羅說蓋本之朱注。其後林雲銘本之,陸樹芝本之,今王氏亦本之。然知薇蕨可食之菜,僅有薇芒,何至傷足,乃易為“棘刺”?然于迷陽終無關也。章太炎雲“陽借為場,迷場,猶迷塗也”,擅改原文,義仍未允。武按:郭云:“迷陽,猶亡陽也。”成云:“陽,明也。”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詐狂。 ”林疑獨本之云:“迷陽,言晦其明。”陸西星亦然,云:“自昧其明。”諸說於義為得,惟郭以亡訓迷為不當耳。考說文:“迷,惑也。”又云:“陽,高明也。 ”詩豳風:“我朱孔陽。”傳:“陽,明也。”白虎通爵論:“陽,猶明也。”蓋莊子之道,在於離形去知。明者,知之所致也,故不尚明。亦如老子大知若愚,玄德、守黑之義。故其言曰“吐爾聰明”,曰“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曰“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曰 “滑欲

中国古代阴阳家有邹衍、驺奭、公梼生、公孙发、南公、乘丘子等。其中以邹衍最为著名。邹衍(约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0年),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亦是五行的创始人。邹衍的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

都匠符三道 凡欲行符先服都匠符若病人服亦先吞此符 堂以当日书此符安膝下纳一符笔管中书符大有验 凡书三部符及一切符同用上符印印诸符 解秽符十一道 二符皇老角殗行符时先吞之 符纳水中漱

阴阳家是先秦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其中心思想为阴阳五行学说,故名。《汉书·艺文志》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阴阳家将古代科学知识和占卜巫术相混杂,他们掌握了自然界变化的一些规律,

论真仙第一 吕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壮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 钟曰:「人之生,自父母交会而二气相合,即精血为胎胞,于太初之后而有太质。阴承阳生,气随胎化,三百日形圆。灵光入

玄要篇 仿古二章 元始祖气,朴朴昏昏。元含无朕,始浑无名。混沌一破,太乙吐萌。两仪合德,日月晦明。乾交坤变,坤索乾成。异名同出,一本共根。内外虚实,刚柔平均。阴阳壁理,变化分形。真精真气,

《汉书·艺文志》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公檮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乘丘子》五篇。六国时。《杜文公》五篇。《黄帝泰素》二十篇……等等,但现存少量残文外,均已亡佚。

阴阳家的思想,主要源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经”。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胡适曾在

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 自赵献书燕王曰:始臣甚恶事,恐赵足……臣之所恶也,国外冒赵而欲说丹与得,事非……臣也。今奉阳〔君〕……封秦也,任秦也,比燕于赵。令秦与〔兑〕……宋不可信,若我其余徐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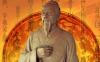
阴阳家的创始人是邹衍。邹衍是道家代表人物、五行学说创始人,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 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余岁。相传墓地在今山东章丘相公庄镇郝庄村。提倡的主要学说是“五行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著有《邹子》一书,《永乐大典》等将

《仙经》云:从半夜子时服九九八十一,鹦呜时八八六十四,日出时六六三十六,食时五五二十五,禺中四四一十六。夫前法是世人及旧经相传,妄为习服,虚役岁月,徒履艰辛,功效无成,久而反损。盖由不服元气,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闲居,曾子侍。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于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孔子不应。曾子

【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

学术 先生谓董遵曰:人得天地之气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须是与天地之体同其广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做得一个人。若天地间有一物不知、一物处置不得,便与天地不相似矣。 学者须是大其心,葢心

童蒙训卷上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 孔子以前,异端未作,虽

穷秀才谴责下人,至鞭扑而极矣。暂行知警,常用则翫,教儿子亦然。 贫人不肯祭祀,不通庆吊,斯贫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絶,是与祖宗不相往来;庆吊絶,是与亲友不相往来。名曰独夫,天人不佑。 凡无子而

迹府 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 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 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

吴从善序 古之君子,学足以开物成务,道足以经纶大经,必思任天下之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措于用也,秩之为礼,宣之为乐,布之为纪纲法度,施之为政刑,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泽被于无穷。此奚特假言

原序 忍乃胸中博闳之器局,为仁者事也,惟宽恕二字能行之。颜子云犯而不校,《书》云有容德乃大,皆忍之谓也。韩信忍于胯下,卒受登坛之拜;张良忍于取履,终有封侯之荣。忍之为义,大矣。惟其能忍则有涵

序 《神农书》一卷,相传炎帝神农氏撰。案《汉书.艺文志.农家.神农》二十篇;《兵阴阳家.神农兵法》一篇;《五行家.神农大幽五行》二十六卷;《杂占家.神农敎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经方家.神农黄

[问]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生异类,本为养人。禁之宰杀,逆天甚矣。[答]既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奈何不知万物为天地之赤子。赤子之中,强凌弱,贵欺贱,父母亦大不乐矣。倘因食其肉,遂谓天所以养我,则虎、豹、蚊、虻,亦食人类血肉,将天之生人

不管《三字经》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在有限篇幅当中赞扬了两位非常有才学的女子,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蔡文姬,而另一位是我们比较陌生的谢道韫。谢道韫是东晋时期著名才女,我们知道有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之家和寻常百姓之家是对着

大家都知道,人最好是从岁数很小时,就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就开始勤奋地学习,就开始接受良师的指导。但人世间的很多事是难以预料的。很多人或说更多的人,因种种原因错过了最佳的读书和受教育年龄。那年岁大的人还应不应学习?年岁大的人学习了还能不能够取

学习离不开刻苦的精神,《三字经》对这点当然不会放过,它也非常强调,所以《三字经》用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稍微有点那么极端的故事,来张扬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我们后来把这两个故事并成一个成语叫悬梁刺

三字经一直是通过讲故事,把一些深刻的道理,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既然是讲学习,谁最合适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谁是一个学习的楷模呢?毫无疑问是孔子。所以接下来三字经讲:昔仲尼,师项橐(驼)。古圣贤,尚勤学。字面意思非常清楚,想当年孔老夫子拜项橐为师

接下来,《三字经》又用12个字讲述了明朝的败亡。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也就是说永乐帝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到了崇祯就在煤山去世,这位皇帝在人世间活了只不过33岁,他是1611年出生,1644年在煤山上吊自杀,不少人认为,崇祯实在并不是一个坏皇

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明太祖,久亲师的故事,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长时间的亲自率领军队进行征战,最后成功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明朝,那么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他是用哪些手段、方法、理念,换句话说,他是怎样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是高度集

根据我所采用的这个版本,元朝以后的明朝是《三字经》讲述的最后一个朝代。一般认为讲述到后来的清朝乃至民国都是后来比较近的人离今天比较近的人增补的所以我们讲《三字经》,在历史部分就讲到明朝。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这样四句12个字是讲述了明太

在中国历史上接着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的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就是元朝,三字经讲元朝时是这么讲的: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并中国,兼戎翟。什么意思呢?到了元朝兴起时金朝也灭亡了,因为金朝是被元朝和南宋联合灭亡的。有宋氏 一同灭,连宋朝捎带着也灭亡了

赵匡胤即位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抗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皇帝的位子还没坐暖呢就御驾亲征,费了不小的劲才把这两个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镇压下去,这件事使赵匡胤心里怎么都不踏实,所以有一天他就单独召见赵普这位自己主要的谋士,跟他商量。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