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正义曰:此篇皆论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尧、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疏]“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正义曰:此章论孔子希言难及之事也。罕,希也。与,及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注“罕者”至“言也”。
○正义曰:《释诂》云:“希,罕也。”转互相训,故罕得为希也。云“利者,义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谓君子利益万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义,法天之利也。云“命者,天之命也”者,谓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穷通、夭寿,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仁者爱人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郑曰:“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郑曰:“闻人美之,承之以谦。吾执御,欲名六艺之卑也。”
[疏]“达巷”至“御矣”。
○正义曰:此章论孔子道艺该博也。“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者,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者,孔子闻人美之,承之以谦,故告谓门弟子曰:“我於六艺之中,何所执守乎?但能执御乎?执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辞。又复谦指云:“吾执御矣。”以为人仆御,是六艺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艺之卑,故云“吾执御矣。”谦之甚矣。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孔曰:“冕,缁布冠也,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纯,丝也。丝易成,故从俭。”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王曰:“臣之与君行礼者,下拜然後升成礼。时臣骄泰,故於上拜。今从下,礼之恭也。”
[疏]“子曰”至“从下”。
○正义曰:此章作孔子从恭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者,冕,缁布冠也。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故云“麻冕,礼也。”今也,谓当孔子时。纯,丝也。丝易成,故云纯,俭。用丝虽不合礼,以其俭易,故孔子从之也。“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者,礼,臣之与君行礼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礼也。今时之臣,皆拜於上长骄泰也。孔子以其骄泰则不孙,故违众而从下拜之礼也。下拜,礼之恭故也。
○注“孔曰”至“从俭”。
○正义曰:云“冕,缁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别号,故冕得为缁布冠也。《士冠礼》曰:“陈服,缁布冠頍项青组,缨属于頍。”记曰:“始冠缁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齐则缁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云“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者,郑注《丧服》云:“布八十缕为升。”
○注“王曰”至“恭也”。
○正义曰:云“臣之与君行礼者,下拜然後升成礼”者,案《燕礼》,君燕卿大夫之礼也。其礼云:“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郑注:“升成拜,复再拜稽首也。先时君辞之,於礼若未成然。”又《觐礼》:“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诸公奉箧服,如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与君行礼,下拜然後升成礼也。
子绝四:毋意,以道为度,故不任意。毋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毋固,无可无不可,故无固行。毋我。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
[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正义曰:此章论孔子绝去四事,与常人异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师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随时用舍,好自专必。惟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专必也。常人之情,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好坚固其所行也。孔子则无可无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异,以擅其身。孔子则述古而不自作处,群众萃聚,和光同尘,而不自异,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包曰:“匡人误围夫子,以为阳虎。阳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颜克时又与虎俱行。後克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与共识克,又夫子容貌与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围之。”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孔曰:“兹,此也。言文王虽已死,其文见在此。此,自谓其身。”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孔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後死。言天将丧此文者,本不当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丧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马曰:“其如予何者,犹言奈我何也。天之未丧此文,则我当传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违天以害已也。”
[疏]“子畏”至“予何”。
○正义曰:此章记孔子知天命也。“子畏於匡”者,谓匡人以兵围孔子,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者,孔子以弟子等畏惧,故以此言谕之。兹,此也。言文王虽已死,其文岂不见在我此身乎?言其文见在我此身也。“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者,後死者,孔子自谓也。以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谓已为後死者。言天将丧此文者,本不当使我与知之。今既使我知之,是天未欲丧此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者,如予何,犹言奈我何也。天之未丧此文,则我当传之。匡人其欲奈我何,言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已也。
○注“包曰”至“围之”。
○正义曰:此注皆约《世家》,述其畏匡之由也。案《世家》云:“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克为仆,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状貌类阳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已下文与此正同,是其事也。
大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吴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艺。”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曰:“言天固纵大圣之德,又使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包曰:“我少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当多能。”
[疏]“大宰”至“多也”。
○正义曰:此章论孔子多小艺也。“大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者,大宰,大夫官名。大宰之意,以为圣人当务大忽小,今夫子既曰圣者与,又何其多能小艺乎?以为疑,故问於子贡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者,将,大也。言天固纵大圣之德,又使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者,孔子闻大宰疑已多能非圣,故云:知我乎。谦谦之意也。“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者,又说以多能之由也。言我自小贫贱,常自执事,故多能为鄙人之事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者,又言圣人君子当多能乎哉?言君子固不当多能也。今已多能,则为非圣,所以为谦谦也。
○注“孔曰”至“小艺”。
○正义曰:云“大宰,大夫官名”者,案《周礼》,大宰六卿之长,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也。云“或吴或宋,未可分也”者,以当时惟吴、宋二国上大夫称大宰,诸国虽有大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吴或宋,未可分也”。郑云“是吴大宰嚭也”。以《左传》哀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又子贡尝适吴,故郑以为是吴大宰嚭也。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郑曰:“牢,弟子子牢也。试,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见用,故多技艺。”
[疏]“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正义曰:此章论孔子多技艺之由,但与前章异时而语,故分之。牢,弟子琴牢也。试,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见用於时,故多能技艺。”
○注“牢,弟子子牢也”。
○正义曰:《家语·弟子篇》云:“琴牢,卫人也,字子开,一字张。”此云弟子子牢,当是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尽,今我诚尽。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来问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则发事之终始两端以语之,竭尽所知,不为有爱。”
[疏]“子曰”至“竭焉”。
○正义曰:此章言孔子教人必尽其诚也。“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所知,不尽以教人乎哉?无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尽,今我诚尽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者,此举无知而诚尽之事也。空空,虚心也。叩,发动也。两端,终始也。言设有鄙贱之夫来问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则发事之终始两端以告语之,竭尽所知,不为有爱。言我教鄙夫尚竭尽所知,况知礼义之弟子乎。明无爱惜乎其意之所知也。
○注“知者”至“诚尽”。
○正义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犹言意之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尽”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以教人,未必竭尽所知,谓多所爱惜也。云“今我诚尽”者,谓孔子言今我教人实尽其意之所知,无爱惜也,故云无知也。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
[疏]“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正义曰:此章言孔子伤时无明君也。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则时无圣人也。故叹曰:“吾已矣夫”,伤不得见也。
○注“孔曰”至“是也”。
○正义曰:云“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者,《礼器》云:“升中於天而凤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鸟兽则凤皇来。”天老曰:“凤象:麟前鹿後,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含鸡喙,五色备举。出於东方君子之国,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见则天下大安宁。”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包曰:“作,起也;趋,疾行也。此夫子哀有丧,尊在位,恤不成人。”
[疏]“子见”至“必趋”。
○正义曰:此章言孔子哀有丧,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齐衰,周亲之丧服也。言齐衰,则斩衰从可知也。冕,冠也,大夫之服也。瞽,盲也。“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者,作,起也;趋,疾行也。言夫子见此三种之人,虽少,坐则必起,行则必趋。
颜渊喟然叹曰:“喟,叹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言不可穷尽。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可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循循,次序貌。诱,进也。言夫子正以此道进劝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开博我,又以礼节节约我,使我欲罢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则又卓然不可及。言已虽蒙夫子之善诱,犹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疏]“颜渊”至“也已”。
○正义曰:此章美夫子之道也。“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喟,叹声也。弥,益也。颜渊喟然发叹,言夫子之道高坚不可穷尽,恍惚不可为形象,故仰而求之则益高,钻研求之则益坚,瞻之似若在前,忽然又复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者,循循,次序貌;诱,进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有次序,可谓善进劝人也。“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者,末,无也。言夫子既开博我以文章,又节约我以礼节,使我欲罢止而不能。已竭尽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创立,则又卓然绝异,已虽欲从之,无由得及。言已虽蒙夫子之善诱,犹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门人为臣。郑曰:“孔子尝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礼。”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孔曰:“少差曰间。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马曰:“无宁,宁也;二三子,门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宁死於弟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孔曰:“君臣礼葬。”予死於道路乎?”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於道路乎?”
[疏]“子疾”至“路乎”。
○正义曰: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疾病”者,疾甚曰病。“子路使门人为臣”者,以孔子尝为鲁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礼,以夫子为大夫君也。“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者,少差曰间。当其疾甚时,子路以门人为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责之,言子路久有是诈欺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者,言我既去大夫,是无臣也。女使门人为臣,是无臣而为有臣。如此行诈,人盖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谁欺。既人不可欺,乃欲远欺天乎?“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无宁,宁也;二三子,门人也。言就使我有臣,且我等其死於臣之手,宁如死於其弟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谓君臣礼葬。言且就使我纵不得以君臣礼葬,有二三子在,我宁当忧弃於道路乎?言必不至死於道路也。
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马曰:“韫,藏也。椟,匮也。谓藏诸匮中沽卖也。得善贾,宁肯卖之邪?”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包曰:“沽之哉,不
衒卖之辞。我居而待贾。”
[疏]“子贡”至“者也”。
○正义曰: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者,子贡欲观孔子圣德藏用何如,故托玉以谘问也。韫,藏也。椟,匮也。诸,之。沽,卖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在椟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贵之贾,宁肯卖之邪?君子於玉比德。子贡之意,言夫子有美德而怀藏之,若人虚心尽礼求之,夫子肯与之乎?“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者,孔子答言,我卖之哉。不
衒卖之辞。虽不衒卖,我居而待贾。言有人虚心尽礼以求我道,我即与之而不吝也。
子欲居九夷。马曰:“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马曰:“君子所居则化。”
[疏]“子欲”至“之有”。
○正义曰:此章论孔子疾中国无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东方之夷有九种。孔子以时无明君,故欲居东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谓孔子言,东夷僻陋无礼,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则化,使有礼义,故云何陋之有。
○注“马曰: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
○正义曰:案《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又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丽,四曰满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郑曰:“反鲁,哀公十一年冬,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
[疏]“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正义曰:此章记孔子言正废乐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鲁,应聘诸国。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也。
○注“反鲁,鲁哀公十一年冬”。
○正义曰:案《左传》哀十一年冬,“卫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杜注云:“於是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於我哉?”马曰:“困,乱也。”
[疏]“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於我哉?”
○正义曰:此章记孔子言忠顺孝悌哀丧慎酒之事也。困,乱也。言出仕朝廷,则尽其忠顺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门,则尽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丧事,则不敢不勉力以从礼也,未尝为酒乱其性也。他人无是行,於我,我独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
[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正义曰:此章记孔子感叹时事既往,不可追复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见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复,故感之而兴叹,言凡时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昼夜而有舍止也。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时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发此言。
[疏]“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正义曰:此章孔子疾时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包曰:“篑,土笼也。此劝人进於道德。为山者,其功虽已多,未成一笼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见其志不遂,故不与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马曰:“平地者将进加功,虽始覆一篑,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据其欲进而与之。”
[疏]“子曰”至“往也”。
○正义曰:此章孔子劝人进於道德也。“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者,篑,土笼也。言人之学道,垂成而止,前功虽多,吾不与也。譬如为山者,其功虽已多,未成一笼,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见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与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者,言人进德修业,功虽未多,而强学不息,则吾与之也。譬如平地者,将进加功,虽始覆一篑,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据其欲进,故吾则往而与之也。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颜渊解,故语之而不惰。馀人不解,故有惰语之时。
[疏]“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正义曰:此章美颜回也。惰,谓懈惰也。言馀人不能尽解,故有懈惰於夫子之语时。其语之而不懈惰者,其唯颜回也与,颜渊解故也。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包曰:“孔子谓颜渊进益未止,痛惜之甚。”
[疏]“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正义曰:此章以颜回早死,孔子於後叹惜之也。孔子谓颜渊进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孔曰:“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
[疏]“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正义曰:此章亦以颜回早卒,孔子痛惜之,为之作譬也。言万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後生谓年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疏]“子曰”至“也已”。
○正义曰:此章劝学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者,後生谓年少也。言年少之人,足以积学成德,诚可畏也,安知将来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时不能积学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名无闻,虽欲强学,终无成德,故不足畏也。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孔曰:“人有过,以正道告之,口无不顺从之,能必自改之,乃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马曰:“巽,恭也。谓恭孙谨敬之言,闻之无不说者,能寻绎行之,乃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疏]“子曰”至“已矣”。
○正义曰:此章贵行也。“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者,谓人有过,以礼法正道之言告语之,当时口无不顺从之者。口虽服从,未足可贵,能必自改之,乃为贵耳。“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者,巽,恭也;绎,寻绎也。谓以恭孙谨敬之言教与之,当时闻之,无不喜说者。虽闻之喜说,未足可贵,必能寻绎其言行之,乃为贵也。“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谓口虽说从,而行不寻绎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末如之何,犹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慎所主友,有过务改,皆所以为益。
[疏]“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正义曰:此章戒人忠信改过也。主犹亲也。惮犹难也。言凡所亲狎,皆须有忠信者也,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苟有其过,无难於改也。《学而篇》已有此文,记者异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曰:“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
[疏]“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正义曰: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帅,谓将也。匹夫,谓庶人也。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贱,但夫妇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曰:“缊,枲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贪求,何用为不善?疾贪恶忮害之诗。”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马曰:“臧,善也。尚复有美於是者,何足以为善?”
[疏]“子曰”至“以臧”。
○正义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者,缊,枲著也。缊袍,衣之贱者。狐貉,裘之贵者。常人之情,著破败之缊袍,与著狐貉之裘者并立,则皆惭耻。而能不耻者,唯其仲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贪求,何用为不善?言仲由不忮害,不贪求,何用为不善?此《诗·邶风·雄雉》之篇,疾贪恶忮害之诗也。孔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终身诵之”者,子路以夫子善已,故常称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孔子见子路诵之不止,惧其伐善,故抑之。言人行尚复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为善?
○注“孔曰:缊,枲著”。
○正义曰:《玉藻》云:“纩为茧,缊为袍。”郑玄云:“衣有著之异名也。纩谓今之新绵,缊谓今纩及旧絮也。”然则今云枲著者,杂用缊麻以著袍也。
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雕伤;平岁则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後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疏]“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
○正义曰:此章喻君子也。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雕伤;若平岁,则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後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能自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子曰:“知者不惑,包曰:“不惑乱。”仁者不忧,孔曰:“无忧患。”勇者不惧。”
[疏]“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正义曰: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乱;仁者知命,故无忧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惧。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适,之也。虽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虽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虽能”有所立,未必能权量其轻重之极。“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逸诗也。唐棣,
栘也,华反而後合。赋此诗者,以言权道反而後至於大顺。思其人而不得见者,其室远也。以言思权而不得见者,其道远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思者,当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为远。能思其反,何远之有!言权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疏]“子曰”至“之有”。
○正义曰:此章论权道也。“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者,适,之也。言人虽可与共学,所学或得异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与也。“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者,言人虽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故未可与也。“可与立,未可与权”者,言人虽能有所立,未必能随时变通权量其轻重之极也。“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者,此逸诗也。唐棣,
栘也,其华偏然反而後合。赋此诗者,以言权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顺也。“岂不尔思”者,言诚思尔也。诚思其人而不得见者,其室远也。以喻思权而不得见者,其道远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者,言夫思者,当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为远。能思其反,何远之有!言权可知,唯不知思尔。傥能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记者嫌与诗言相乱,故重言“子曰”也。
○注“唐棣,栘也”。
○正义曰:《释木》文也。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璞曰:“似白杨,江东呼夫栘。《诗·召南》云:唐棣之华。”陆机云:“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车下李。所在山皆有其华,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翻译:孔子说:学习并时常温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从心里感到高兴吗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知止(4)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孔子说:学习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是件高兴的事吗?有好朋友从远方来(互相切磋,增长学问),不是件快乐的事吗?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怨恨别人,不也是有道德的表现吗? 2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翻译】孔子说:“学习了知识又时常实践,不也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知道)我,我却不怨恨(生气)

夫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战国初兴,至化陵迟,异端并作,仪、衍肆其诡辩,杨、墨饰其淫辞。遂致王公纳其谋,以纷乱於上;学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犹洚水怀山,时尽昏垫,繁芜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

《礼记正义》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汉代有郑玄作注,唐代有孔颖达为之正义,都是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阅读研究《礼记》的重要版本。今归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由吕友仁先生拟影印宋绍熙刻本《礼记正义》校以

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又称论语注疏解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二十卷。案何注皇疏皆以道家思想解论语,又於名物制度无所考订,颇为学人所不满。北宋时遂由朝廷於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昺删除皇疏之文,而归向儒学本来之义理,又加名物制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春秋左氏》,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左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

谦受益,满招损,谦虚纳百福。成功的人物没有不谦虚的,不谦虚就会很快失败。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而拜,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谦虚得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呵护,就连鬼神都呵护它。“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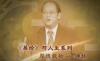
坤卦是八卦中至柔至顺的一卦。由六个阴爻组成,底部三个阴爻为下坤卦,上面三个阴爻为上坤卦。由下到上依次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坤卦的卦辞:元、亨、利牝(bi母)马贞。用母代表坤卦,用马代表健行,有恒心。每一个人都有阴性的魂和阳性的魂。

第四讲:自强不息——乾卦,乾卦是天下第一卦,代表生命的开始。乾卦由由下到上六条横线组成,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一到九的奇数代表阳,偶数代表阴,九最大代表无穷的力量,六居中代表安静。在古代,龙是三栖动物。

第三讲:八卦的卦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相互转化。“女子虽弱,为母则强”。八个卦象的写法: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巽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第二讲:《易经》的由来,易经的发展三位圣人:伏羲氏、周文王和孔子做了巨大的贡献。开天辟地之后,人要怎样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和发展,让伏羲氏产生了忧患意识,易经起源于忧患。易经的核心是居安思危。伏羲氏抬头观天象,观察天体的运转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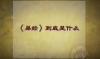
第一讲:《易经》是什么?易经是“不学不会,学了不一定会,会来终身受用”。易经的重点是修德行善。易经包括义理和象数。义理指为人处事的道理;象数指卦象的计算规律。易经是“观天道立人道”,真正的儒家是由内而发,西方有哲学派别认为“人是唯一使用符号的动物”。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lè)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学而》) 2 曾子曰:吾(wú)日三省(xǐng)吾(wú)身,

一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

[问]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生异类,本为养人。禁之宰杀,逆天甚矣。[答]既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奈何不知万物为天地之赤子。赤子之中,强凌弱,贵欺贱,父母亦大不乐矣。倘因食其肉,遂谓天所以养我,则虎、豹、蚊、虻,亦食人类血肉,将天之生人

不管《三字经》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在有限篇幅当中赞扬了两位非常有才学的女子,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蔡文姬,而另一位是我们比较陌生的谢道韫。谢道韫是东晋时期著名才女,我们知道有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之家和寻常百姓之家是对着

大家都知道,人最好是从岁数很小时,就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就开始勤奋地学习,就开始接受良师的指导。但人世间的很多事是难以预料的。很多人或说更多的人,因种种原因错过了最佳的读书和受教育年龄。那年岁大的人还应不应学习?年岁大的人学习了还能不能够取

学习离不开刻苦的精神,《三字经》对这点当然不会放过,它也非常强调,所以《三字经》用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稍微有点那么极端的故事,来张扬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我们后来把这两个故事并成一个成语叫悬梁刺

三字经一直是通过讲故事,把一些深刻的道理,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既然是讲学习,谁最合适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谁是一个学习的楷模呢?毫无疑问是孔子。所以接下来三字经讲:昔仲尼,师项橐(驼)。古圣贤,尚勤学。字面意思非常清楚,想当年孔老夫子拜项橐为师

接下来,《三字经》又用12个字讲述了明朝的败亡。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也就是说永乐帝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到了崇祯就在煤山去世,这位皇帝在人世间活了只不过33岁,他是1611年出生,1644年在煤山上吊自杀,不少人认为,崇祯实在并不是一个坏皇

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明太祖,久亲师的故事,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长时间的亲自率领军队进行征战,最后成功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明朝,那么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他是用哪些手段、方法、理念,换句话说,他是怎样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是高度集

根据我所采用的这个版本,元朝以后的明朝是《三字经》讲述的最后一个朝代。一般认为讲述到后来的清朝乃至民国都是后来比较近的人离今天比较近的人增补的所以我们讲《三字经》,在历史部分就讲到明朝。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这样四句12个字是讲述了明太

在中国历史上接着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的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就是元朝,三字经讲元朝时是这么讲的: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并中国,兼戎翟。什么意思呢?到了元朝兴起时金朝也灭亡了,因为金朝是被元朝和南宋联合灭亡的。有宋氏 一同灭,连宋朝捎带着也灭亡了

赵匡胤即位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抗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皇帝的位子还没坐暖呢就御驾亲征,费了不小的劲才把这两个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镇压下去,这件事使赵匡胤心里怎么都不踏实,所以有一天他就单独召见赵普这位自己主要的谋士,跟他商量。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