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本《心经》略释
《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praj?āpāramitāhr?ayasūtra),因为二百六十个字的《心经》体现了《般若经》的心髓,所以略称为《心经》。该经的空义,反映秦译《大品般若经》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内容,相当于唐译《大般若经》的第401卷至405卷的内容。
《心经》的译本很多,流行本是唐玄奘译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相传在玄奘译本之前,有姚秦鸠摩罗什译于公元402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明咒经》,学术界对此提出异议。[1]唐玄奘以后的译本主要如下:唐义净译于公元700年的《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法月译于公元733年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般若和利言合作译于公元790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智慧轮译于公元850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施护译于公元980年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翻译年代不详的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除此之外,还有音译敦煌石室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日本大藏经本《梵语心经》。译自藏文的《心经》有四种:日僧能海宽由藏文译为日文,再由日文转译为汉文的《般若心经》、孙慧风译《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楚禅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超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心经》的注释本很多,主要如下:唐代窥基的《心经幽赞》、法藏的《心经略疏》、圆测的《心经赞》、宋代智圆的《心经疏》、明代元贤德《心经指掌》、清代续法的《心经事观解》、近代太虚的《心经浅注》等。[2]
本文对梵文《心经》逐字逐句进行解释,并与玄奘译本进行对照,与玄奘译本有些出入,原因何在?可能与玄奘译本所依据的梵文底本不同。玄奘译本所依据的梵文底本至今不得而知,所以很难对此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nama? sarvaj?āya
译:向知一切者(佛)致敬!
注:nama?原形是namas,是带有动词属性的中性名词,往往作不变词,要求有关的名词变为为格。sarvaj?āya,阳性、单数、为格,原形是sarvaj?a,由两个词构成:sarva(一切)十√j?ā(知,变为复合词后,ā变为a),构成依主释,指具有一切智而知一切的佛。
释:这种“致敬词”往往出现于论典之首,因为论是菩萨造的,菩萨为了表示对佛的尊重,表明自己的论绝无违佛之意,所以首先向佛致敬。这种“致敬词”不应当出现于经首,因为经是佛说的。佛具谦虚美德,不能是自己向自己致敬,也不引导他人向自己致敬。现存《心经》汉译本都没有这种“致敬词”,这是合理的。《心经》不同于一般佛经,它是《般若经》的心髓,经过后人的节选加工,这种“致敬词”可能出于节选加工者之手。
āryāvalokite?varabodhisattvo ga?bhīrāyā? praj?āpāramitāyā? caryā? caramāno vyavalokayati sma · pa?ca skandhā? · tā??ca svabhāva?ūnyān pa?yati sma ·
译:神圣的观自在菩萨,于深般若般若波罗蜜多修行的时候,照见五蕴,其自性是空的。
注:āryāvalokite?varabodhisattva?(神圣的观自在菩萨,a?因遇浊音g,变为o),是复合词,从整体来讲,是持业释。是阳性、单数、体格,是本句主语。
avalokite?varabodhisattva?(观自在)是复合词,由avalokita(观)十ī?vara(自在)构成,是持业释。有人认为avalokite?vara(观自在)是avalokitasvara(观世音)之误,有些牵强。梵文《妙法连华经》等佛经中的“观世音”都是avalokite?vara(确切的翻译应当是观自在),不能说都是“误”。而且,svara这个词有“声音”的意思,没有“世”的意思,所以avalokitasvara不能译成“观世音”。
众所周知,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很善于意译,观自在菩萨救苦救难,有神通,六根互用,一般人是“听”声音,他是“观”声音。世人遇难,只要呼唤他的名字,他就“观”其声音,寻声往救。鸠摩罗什据此译成观世音,顺理成章,更能表达这位菩萨的特征,更便于在佛教徒中流行。
avalokite?vara是阳性名词,由此可见,观自在菩萨或观世音菩萨是男性,女相是他的化身。
bodhisattva(菩萨,觉有情)也是复合词,由bodhi(觉悟)和sattva(有情)两个词构成,是依主释,意为“有觉悟的有情”。
该复合词玄奘译为:“观自在菩萨”,却形容词“神圣的”(ārya)。
ga?bhīrāyā? praj?āpāramitāyā? caryā? caramā?a?(a?因遇浊音v,所以变为o),是时间状语从句。
译:“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修行的时候”。
注:praj?āpāramitāyām(m因遇辅音c,所以变为?)是阴性、单数、依格,由prajnā(般若)和pāramitā(波罗密多)两个词构成一个复合词,是持业释。ga?bhīrāyām(m因遇辅音p,所以变为?)是形容词,是praj?āpāramitāyām的定语,与praj?āpāramitāyām同性、同数、同格。
caryām(m因遇辅音c,所以变为?)是caramā?a?(a?因遇浊音v,所以变为o)的宾语,是阴性、单数、业格。caramā?a?是现在分词中间语态,现在分词具有形容词的作用,与主语同性、同数、同格,即阳性、单数、体格,其动作是:在……的时候。
本段玄奘译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梵本一致。
vyavalokayati sma和后边的pa?yati sma是谓语,sma是不变词,表示“过去”。vyavalokayati(照)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原形是vi+ava+√luk,第十类动词。pa?yati也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原形是d??,第四类动词。
svabhāva?ūnyān(形容词,自性是空的)是说明tān的,与tān同性、同数、同格,即阳性、复数、业格,由svabhāva(自性)和?ūnya(空的)两个词构成,这个复合词是持业释。Svabhāva也是个复合词,由sva(自)和bhāva(性)两个词构成,这个复合词也是持业释。
本段玄奘以为:“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玄奘译本中的“度一切苦厄”在梵文本中是没有的。根据上述分析,应译为:“照见五蕴,其自性是空的。”
iha ?āriputra rūpa? ?ūnyatā ?ūnyataiva rūpa? rūpānna p?thak ?ūnyatā ?ūnyatāyā na p?thagrūpa? yadrūpa? sā ?ūnyatā yā ?ūnyatā tadrūpa?·
译:在此,舍利子!色是空性,空性就是色;空性不异于色,色不异于空性;凡是色,都是空性;凡是空性,都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这样。
注:iha是不变词,意思是“在这里”。?āriputra是阳性、单数、呼格。
rūpa?和?ūnyatā构成一句话,意思是“色是空性”。rūpa?(色)是中性、单数、体格,?ūnyatā(空性)是阴性、单数、体格,?ūnya(空的)是形容词,加tā变为抽象名词,所以译为“空性”。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是)。
同样,?ūnyataiva rūpa?也是一句话,意思是“空性就是色”。?ūnyataiva是?ūnyatā(空性,阴性、单数、体格)加eva(不变词,就),rūpa?是中性、单数、体格,也是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
rūpānna p?thak ?ūnyatā构成一句话,意思是“空性不异于色”。rūpāt是中性、单数、从格,因遇鼻音n,所以变为n。na是不变词,意思是“不”。p?thak是不变词,意思是“异于”,要求与之相关的rūpa(色)变为从格。?ūnyatā是阴性、单数、体格。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
?ūnyatāyā na p?thagrūpam构成一句话,意思是“色不异于空性”。?ūnyatāyā?是阴性、单数、从格,ā?因遇浊音n,所以变为ā。k因遇浊音r,所以变为g。rūpam是中性、单数、体格,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
yad rūpa? sā ?ūnyatā构成一句话,意思是“凡是色,都是空性”。yad…tad…是个词组,其意为:“凡是……都是……”。rūpam是中性、单数、体格,yad是关系代词,与rūpam同性、同数、同格,即中性、单数、体格。?ūnyatā(空性)是阴性、单数、体格,代词sā与其代表的?ūnyatā同性、同数、同格,即阴性、单数、体格。
yā ?ūnyatā tad rūpa?构成一句话,意思是“凡是空性,都是色”。?ūnyatā是阴性、单数、体格,关系代词yā与?ūnyatā同性、同数、同格。rūpam是中性、单数、体格,代词tad与其代表的rūpam同性、同数、同格。
evameva vedanāsa?j?āsa?skāravij?ānāni构成一句话,意思是“受、想、行、识,就是这样”。evam(这样)和eva(就)都是不变词,vedanāsa?j?āsa?skāravij?ānāni是复合词,由vedanā(受,阴性)、sa?j?ā(想,阴性)、sa?skāra(行,阳性)、vij?ānā(识,中性)四个名词并列构成,所以是相违释,复合词的性别以最后一个词vij?āna为准,这个相违释是中性、复数、体格,本句省略动词santi或bhavanti(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复数、第三人称。
本段玄奘译为:“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应视为意译。
iha ?āriputra sarvadharmā? ?ūnyatālak?a?ā anutpannā aniruddhā amalā na vimalā nonā na paripūr?ā?·
译:在此,舍利子!一切法都以空性为相,不生不灭,不染不净,不减不增。
注:iha(在此)是不变词,?āriputra(佛的大弟子舍利子,另译舍利弗)是阳性、单数、呼格。
sarvadharmā?是本句主语,是阳性、复数、体格。这是一个复合词,由sarva(一切,形容词)dharma(法,名词)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意思是“一切法”。
?ūnyatālak?a?ā?(ā?因遇元音a,所以变为ā)是复合词,由?ūnyatā(空性,阴性)lak?a?a(相,中性)两个词构成,是多财释,作形容词,与主语sarvadharmā?同性、同数、同格,即阳性、复数、体格,此中省略动词santi或bhavanti(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复数、第三人称。本段以下都作此解释。
ud+√pad,意为“生”。utpanna是其过去分词,名词或形容词(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都可以作形容词用)前加a,便是否定。以元音开头的词加an,所以anutpanna的意思是“不生”。有否定词头a或an的复合词,属于依主释。
ni+√rudh,意思是“灭”。niruddha是其过去分词,加否定词an构成aniruddha,意思是
“不灭”。如前所述,这种复合词视依主释。
mala,意为“染”,加否定词头a而成amala,意为“不染”。如前所述,这种复合词是依主释。前缀vi意为“离开”,所以vimala意为“离染”,即“净”。加前缀的词不同于加否定词头a或an,不是复合词。
本段玄奘译为:“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与梵本基本一致。
tasmācchāriputra ?ūnyatāya? na rūpa? na vedanā na sa?j?ā na sa?skārā na vij?ānāni na cak?u??rotraghrā?ajihvākāyamanā?si na rūpa?abdagandharasaspra??avyadharmā? na cak?ur- dhāturyāva?na manovij?ānadhātu? nāvidyā nāvidyāk?ayo yāvanna jarāmara?a? na jarāmara?ak?ayo na du?khasamudayanirodhamārgā na j?ā?a? na prāptirtasmādaprāptitvādb odhisattvasya praj?āpāramitāmā?ritya viharatyacittāvara?a?
译:因此,舍利子!在空性当中没有色,没有受,没有想,没有行,没有识。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界,乃至于没有意识界。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乃至于没有老死,也没有老死尽。没有苦、集、灭、道,没有智,也没有得。因为没有所得性,所以要依靠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而安住,心无阻碍。
注:tasnāt是代词tad的中性、单数、从格,做副词用,意为“因此”。尾音辅音t在初音?前,尾音t变为c,而?则变为ch。?āriputra是阳性、单数、呼格。
?ūnyatāyam(m因遇辅音n,所以变为?,下同)是阴性、单数、依格。na是不变词,意为“不”。rūpam是中性、单数、体格。本句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下同。所以本句意为:“在空性当中没有色”。
vedanā是阴性、单数、体格,接上句的?ūnyatāyam,下同。
sa?j?ā是阴性、单数、体格,sa?skārā?(ā?因遇浊音n,所以变为ā)是阳性、复数、体格。vij?ānāni(识)是中性、复数、体格。rūpam(色)、vedanā(受)、sa?j?ā(想)用单数,可以理解为集体名词,sa?skārā?(行)和vij?ānāni(识)用复数,可以理解为个体名词。
cak?u??rotraghrā?ajihvākāyamanā?si是中性、复数、体格,是复合词,由cak?us(眼,中性)、?rotra(耳,中性)、ghrā?a(鼻,中性)、jihvā(舌,阴性)、kāya(身,中性)、manas(意,中性)六个词构成,是相违释。其性别以最后一个词manas为准,所以是中性。此中省略santi或bhavan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复数、第三人称,本段以下亦依此解释。
同样,rūpa?abdagandharasaspra??avyadharmā?是阳性、复数、体格,这个复合词也是相违释,由rūpa(色,中性)、?abda(声,阳性)、gandha(香,阳性)、rasa(味,阳性)、spra??avya(触,中性)、dharma(法,阳性)六个词构成,这种复合词的性别以最后一个词dharma为准,所以是阳性。本句省略动词santi或bhavanti(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复数、第三人称。
cak?urdhātu?(?在非a、ā的元音后,变为r)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由cak?us(眼,中性,在复合词中,s变为?,在非a、ā的元音后,?变为r)和dhātu(界,阳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因为这两个词是同位语关系,眼根是十八界之一。整个复合词的性别以最后一个词dhātu为准,所以是阳性。此中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na是不变词,意思是“没”。
yāvat(以至于)是不变词,t因遇鼻音n,所以被同化为n。na也是不变词,其意为“没”,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
manovij?ānadhātu?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由manas(意,中性)、vij?āna(识,中性)、dhātu(界,阳性)三个词构成,从整体来讲是持业释,因为manovij?āna(意识)和dhātu(界)是同位语。Manovij?āna也是一个复合词,由manas(as在复合词中变为a?,因遇浊音v,所以变为o)和vij?ān两个词构成一个复合词,意为“意识”,即依靠意根所产生的识,所以是依主释。
nāvidyā是一句话,意思是“没有无明”。这句话只有两个词:na(没,不变词)和avidyā(无明,阴性、单数、体格),a加a,变为ā,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vidyā意为“明”,加否定词头a而成依主释复合词avidyā(无明)。
nāvidyāk?aya?(a?因遇浊音y,变为o)是一句话,意思是“没有无明尽”。这句话只有两个词:na(没,不变词)和avidyāk?aya?(无明尽,阳性、单数、体格),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avidyāk?aya?是依主释复合词。
yāvanna jarāmara?am(m因遇辅音n,变为?)构成一句话,意思是“乃至于没有老死”。yāvat(乃至于,t因遇辅音n,被同化为n)和na(没)都是不变词。jarāmara?am(老死,m因遇辅音n,变为?)是复合词,中性、单数、体格。由jarā(老,阴性)和mara?a(死,中性)两个并列的名词构成相违释,意思是“老死(m因遇辅音n,变为?)”,其性别以最后一个词mara?a为准,所以是中性,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
na jarāmara?ak?aya?(a?因遇浊音n,变为o)构成一句话,na(没)是不变词,jarāmara?ak?aya?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从整体来讲是依主释,jarāmara?a是由两个并列的名词所构成的相违释复合词。此中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本句的意思是:没有老死尽。
na du?khasamudayanirodhamārgā?(ā?因遇浊音n,变为ā)构成一句话,意思是:没有苦、集、灭、道。na是不变词,意思是“没”。du?khasamudayanirodhamārgā?是阳性、复数、体格,这个复合词由du?kha(苦,中性)、samudaya(集,阳性)、nirodha(灭,阳性)、mārga(道,阳性)四个并列名词构成,所以是相违释。其性别以最后一个词mārga为准,所以是阳性,此中省略动词santi或bhavan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复数、第三人称。
na j?ā?am构成一句话,意思是:没有智。na是不变词,意思是“没”。j?ā?am(m因遇辅音n,变为?)是中性、单数、体格。j?āna的动词词根是√j?ā(知),j?āna是其过去分词变成的名词,此中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
na prāpti?(?在非a、ā的元音后,变为r)构成一句话,意思是:没有得。na是不变词,意思是“没”。prāpti?(得)阴性、单数、体格。此中省略asti或bhavati(有),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
tasmādaprāptitvādbodhisattvasya praj?āpāramitāmā?ritya viharatyacittāvara?a?构成一句话,意思是:“由于没有这种所得性,所以要依靠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而安住,没有心得阻碍。”tasmāt(t因遇元音a,变为d)和aprāptitvāt(t因遇元音a,变为d)是本句的状语,aprāptitvāt是中性、单数、从格,aprāptitva(无所得性)是名词aprāpti加tva构成,名词加tva和加tā一样构成抽象名词,所不同的是加tā构成阴性名词,加tva构成中性名词。代词tasmāt与它所代表的aprāptitvāt同性、同数、同格,即阳性、单数、从格。
bodhisattvasya是阳性、单数、属格,意为“菩萨的”。praj?āpāramitām是阴性、单数、业格,作ā?ritya的宾语。这个复合词由praj?ā(般若,阴性)和pāramitā(波罗密多,阴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因为这两个词是同位语关系。ā?ritya是独立词,表示先于本句所表达主要动作的动作,用独立词,ā?ritya(依靠)先于主要动词viharati(住)。viharati(住)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动词词根是vi+√h?,第一类动词。
acittāvara?a?是阳性、单数、体格,citta(心,中性)和āvara?a(阻碍)构成依主释,加否定词a,又构成依主释。
本段玄奘译为:“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与梵本基本一致。
cittānara?anāstitvādatrasto viparyāsātikrānto ni??hanirvā?a?。
译:因为心阻碍的不存在性,所以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
注:cittānara?anāstitvāt(t因遇元音a,所以变为d)是中性、单数、从格,这个复合词由citta(心,中性)、āvara?a(阻碍,阳性)、nāstitva(不存在性,中性)三个词构成,是依主释,前两个词也构成依主释。其性别由最后一个词nāstitva为准,所以是中性。nāstitva是由nāsti(不存在,不变词)加tva构成中性抽象名词,意思是“不存在性”。
atrasta?(a?因遇浊音v,所以变为o)是阳性、单数、体格,trasta是动词√tras(恐怖,第二类动词)的过去分词,加否定词头a构成依主释复合词,意思是“不恐怖”。
viparyāsātikrānta?(a?因遇浊音n,所以变为o)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是依主释,由viparyāsa(颠倒梦想,阳性)atikrānta和两个词构成。atikrānta是ati+√kram的过去分词。
ni??hanirvā?a?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是持业释。由ni??ha(究竟,形容词)和nirvā?a?(涅磐,阳性)两个词构成。
本段玄奘译为:“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磐。”与梵本完全一致。
tryadhvavyavasthitā? sarvabuddhā? praj?āpāramitāmā?rityānuttarā? samyaksa?bod- himabhisa?buddhā?.
译:位于三世的一切佛,依靠般若波罗蜜多,认识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注:sarvabuddhā?(一切佛)是本句主语,是阳性、复数、体格,这个复合词由sarva(一切,形容词)和buddha(佛,阳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
tryadhvavyavasthitā?与主语sarvabuddhā?同性、同数、同格,即阳性、复数、体格,这个复合词是由tryadhva(三世)和vyavasthita(位于)两个词构成,是依主释。vyavasthita是vi+ava+√sthā的过去分词。
praj?āpāramitām是阴性、单数、业格,是动词ā?ritya的动作对象。这个复合词是由praj?ā(般若,阴性)和pāramitā(波罗密多,阴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因为这两个词是同位语关系。ā?ritya是ā+√?ri的独立词,它先于本句的主要动词abhisa?buddha。
samyaksa?bodhi(意译正等觉,音译三藐三菩提)是阴性、单数、业格,这个复合词是由samyak(正确的)和sa?bodhi(意译觉悟,音译三菩提,阴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
anuttara意译无上的,即最高的,音译阿耨多罗。这个形容词是samyaksa?bodhi的定语,与samyaksa?bodhi同性、同数、同格,即阴性、单数、业格。这个词是由uttara(上的)加否定词头an,构成依主释复合词。
abhisa?buddhā?是阳性、复数、体格,这个词是abhi+sam+√budh的过去分词。这种过去分词有形容词的属性,所以要与主语sarvabuddhā?同性、同数、同格。又具有动词属性,所以有宾语anuttarām sa?yaksa?bodhim。
本段玄奘译为:“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梵本完全一致。
tasmājj?ātavya? praj?āpāramitā mahāmantro mahāvidyāmantro ‘nuttaramantro ‘samasamamantra? sarvadu?khapra?amana? satyamamithyatvāt. praj?āpāramitāyāmukto mantra?.
译:因此,应当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是出自不虚妄性的真理,所以要于般若波罗蜜多中说咒。
注:tasmāt(t被j同化为颚音)是指示代词tad的中性、单数、从格,意为“因此”,作副词用。j?ātavyam(m因遇辅音p,变为?)是中性、单数、体格,此中省略指示代词idam(中性、单数、体格),意为“这件事”。
动词√j?ā(知道)加tavya变成一个动形容词,本句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
praj?āpāramitā是阴性、单数、体格,是本句主语。这个复合词由praj?ā(般若,阴性)和pāramitā(波罗蜜多,阴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因为这两个词是同位语关系。
mahāmantra?(a?在浊音m前,变为o)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是由mahat
(大,在复合词中用mahā)和mantra(咒或神咒,阳性)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此中省略动词asti或bhavati(是),现在时、陈述语气、主动语态、单数、第三人称。本句以下亦作此解释。
mahāvidyāmantra?(a?遇元音a,所以变为o)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是由mahat(大)、vidyā(明)、mantra(咒)三个词构成,是持业释。
anuttaramantra?,初音a在o后面消逝,代之以avagraha,a?在元音a前变为o,是阳性、单数、体格,这个复合词是由anuttara(无上)和mantra(咒)两个词构成,是持业释。
asamasamamantra?是阳性、单数、体格,初音a在o后面消逝,代之以avagraha,复合词samasamamantra(等等咒)是持业释,加否定词头a构成依主释。
sarvadu?khapra?amana?是阳性、单数、体格,复合词sarvadu?kha(一切苦)是持业释,复合词sarvadu?khapra?amana(能除一切苦)是依主释。
satyam(不虚妄)是中性、单数、体格。amithyatvāt(不虚妄性)是中性、单数、从格。这个词是amithya(不虚妄)加tva构成的中性抽象名词。
praj?āpāramitāyām(般若波罗蜜多,持业释)是阴性、单数、依格。ukto(a?在浊音m前变为o)是阳性、单数、体格。ukto是动词√vac的过去分词。过去分词除表示过去以外,还有被动的意思。mantra?是阳性、单数、体格。
本段玄奘译为:“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虚,故说波罗蜜多咒。”与梵本完全一致。
tadyathā 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gate bodhisvāhā.
译:说咒如下:“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速证菩提吧!”
注:两个gate都是阴性、单数、呼格,pāragate也是阴性、单数、呼格,这个复合词由pāra(彼岸,阳性)和gati(去,阴性)两个词构成,是依主释。bodhi意译觉悟,音译菩提,阳性名词。svāhā是感叹词,又有“速得”的意思。
本段玄奘翻译如下:“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与梵本完全一致。
iti praj?āpāramitāh?dayasutra? samāptam
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至此结束。
注:iti是不变词,意为“如上”,又相当于引号。复合词praj?āpāramitāh?dayasūtra由praj?ā(般若,阴性)、pāramitā(波罗蜜多,阴性),h?daya(心,中性)、sūtra(经,中性)四个词构成,是持业释。这是经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语题名在开头,梵文与其相反,置于最后。samāptam是中性、单数、体格,意为“结束”,由sam+√āp的过去分词构成。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是般若经系列中一部言简义丰、博大精深、提纲挈领、极为重要的经典,为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现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译本为最流行。整段话的概略意思是“透过心量广大的通达智慧,而超脱世俗困苦的根本途径”。

心经原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常诵心经的好处:增长大智慧,福报,能去除贪、嗔、痴。小学生至大学生常诵增长记忆力,学业、事业、婚姻顺利、心想事成,功德无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佛教大乘教典中,一部文字最短少,诠理最深奥微妙的经典。仅以二百六十个字,浓缩了六百卷大般若经的要义,摄尽了释遵二十二年般若谈的精华,即阐明宇宙人生缘起性空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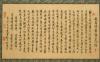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心经何故无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等六种成就,以证明是佛说呢?唐朝唐太宗时,有一位国师名玄奘法师,在家姓陈,十二岁时跟随哥哥出家,出了家后,读一切经典,有些经典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有些经典是别的法师翻译,他对有些语句生疑,很想到印度取经,后来在四川成都挂单,遇到一位老和

回向文1:1、如果时间紧,可以这样回向:弟子__愿以此所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__部之功德,回向给弟子__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历代宗亲。祈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等诸佛菩萨、慈悲作主,超拔他们,令业障消除,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弟子__真心求忏悔(三称磕头)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完整注音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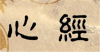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运用智慧观察),照见五蕴皆空(了知身心俱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香声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

心经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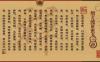
(1)上香 香赞 炉香乍爇,法界蒙熏,诸佛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三称)(2)礼拜 鞠躬或叩拜:礼敬之时,须恭敬至诚。也可默念:能礼所礼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帝珠,一切如来影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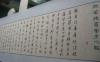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色即是空”是《心经》里的一句话,色即是空后面还有一句是“空即是色”,是说所有的色法。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一张桌子,看起来有这个色相,可是如果你用佛法的角度来看:第一,桌子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没有真实的东西。第二,这张桌子是无常的,就算五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都不会坏,可是终究有一天还是会坏,因为它的本质

“心”,在《心经》中有诸多含义,如心脏、核心、常住真心等。中国人喜欢简略,往往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心经》,在经题中略称“心”,是为了凸显此经的重要性,就好比“心脏”对人的意义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九年,二十二年谈般若,足以见得,般若部是佛法的核心,般若部的核心即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的核心即是

话说玄奘大师来到四川益州,挂单在空惠寺,在那里遇到了一位生病的出家人,大师悉心照顾。一次交谈中,大师提起自己将去天竺等国学法取经之事。那位僧人听后慨叹说:“为了求法而不顾个人安危,真是非常少见。但天竺路途遥远,总在十万里以上,路上有流沙、深水,漫无人迹,只有

外国人他虽然不了解《心经》的意思,但他按照《心经》的音节一直这样持诵下去,绝对比我们理解意思的人修行速度快得多,也高妙得多。比如说咒语都是印度的梵音。在印度人眼中,我们就是外国人。我们现在持咒难道就不起作用吗?不仅有作用,而且好像持咒的感应和摄受力更大一些呢。

“受蕴”是以领纳为义。当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感受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境界,继而产生眼耳鼻舌身五识。如果感受到自己喜欢的境界,那就是顺境,顺境会让人产生贪爱之心;如果感受到自己讨厌的境界,那就是逆境,逆境会让人生起嗔恨之心。当然也会有既不喜欢也不讨厌的境界,这种即是中性的感受。受蕴是人对客观环境的一种情绪

观自在菩萨即是通过闻思修三慧的修持,证得实相智慧,而得大自在。菩萨的修持纲要是六度法门,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梵语中称六度为“六波罗蜜”。此地经文中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与“深般若”即是指菩萨所修学的六波罗蜜法。“行”是指的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深般若”是指最后的

《心经》的人题是“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唐”即唐朝,是翻译这本《心经》的年代。“三藏”是指法师的学识。“藏”是含摄之义,“三藏”即经、律、论三藏。所谓的“经藏”,即记载了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等的言教,所阐述的是佛教的根本教义戒、定、慧三学。

诵《心经》有什么好处?第一点好处:“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所以诵这个《心经》可以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三宝的加持,可以解除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自己办不到的事情,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助我们一臂之力,能得到心灵的安慰。这个在佛法当中来讲这是小利益。

《心经》中有这样四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实际上这四句话是佛祖讲给四种不同的人听的。 第一句:“色不异空”,是讲给凡夫听的。凡夫执着一切都是实有。凡夫把自身的眼耳鼻舌身意当作真实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认为是真实的。实际上眼耳

佛教徒读《心经》,社会人士也读《心经》,《心经》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心经》中的名句很多,其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可以说是名句中的名句。也是非常深奥的一句话,也是整卷《心经》的中心思想。

《大宝积经》,共一百二十卷,是一部丛书体裁的经集,收在《大正藏》第十一册。玄奘在示寂前一年(663)曾试译过几行,因为体力不支不得不停顿下来。菩提流志从神龙二年(706)开始编译,历时七载,在先天二年(713)完毕,完成了玄奘未尽的伟业。他利用《宝积经》

《圆觉经》,是描述如来境界、阐扬诸法实相、彰显圆满觉性的重要经典,素有『三藏十二部的眼目』之称。经文阐述了一切法都是圆觉妙心的显现,每一法都周遍法界,觉性同样也是周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道理。指出:众生与佛,觉性平等,没有差异,只是因为

这首偈的大意是说:当菩萨(发大心的修行者)见到论议人时,就会发愿,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以佛陀的正法,摧伏外道的邪见和论议。见论议人:“论议”是说通过问答的形式等,分别阐述诸法的义理。其目的是使对方了解论理,明了法义,重在显明真理。佛在世时,比丘们常常就某一义理或论题等展开论议。著名的迦旃延尊者就是因为思惟敏捷,辩才无碍

这一愿的大意是说:当菩萨(发大心的修行者)见到身无铠甲、手无兵仗的军人时就会发愿,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永远舍离不善的身口意三业,趣于善道。见无铠仗:“铠”即铠甲。古时战斗中穿戴的铠甲战衣,可以防身。“仗”是弓、矛、剑、戟等兵器的总称,即兵仗、器仗。

此时世尊思维此梵志性格儒雅纯善质直,常为了求知而来请问,不是来惹麻烦的。他如果要问应当随意回答。佛就说:犊子。善哉善哉。随意提问吧,我会回答的。

这时世尊告诉憍陈如:色是无常。因灭色而获得解脱常住之色,受想行识也是无常。因灭此识而获得解脱常住之识。憍陈如。色即是苦,因灭此色而获得解脱安乐之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憍陈如。色即是空,因灭空色而获得解脱非空之色。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居士问:《金刚经》上说:“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何理解请师父开示!一如师父答:把所有的虚妄,就是一切相都是因缘和合的,所有的像都是生灭的变化的,无常的,他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对我们众生来说第一个就是破相证性。因为相是一个虚幻,因缘和合的假象。

迦叶菩萨说:世尊。一切法的意思不确定。为什么呢?如来有时说是善不善。有时说为四念处观。有时说是十二入。有时说是善知识。有时说是十二因缘。有时说是众生。有时说是正见邪见。有时说十二部经。有时说即是二谛。

善男子。虚空之性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佛性也一样。善男子。虚空非过去,因为无现在。法如果有现在则可说过去,因无现在所以无过去,也无现在,因为无未来,法如果有未来则可说现在,因无未来所以无现在也。

《宝积经》与《般若经》、《大集经》、《华严经》、《涅槃经》,并称为大乘佛教经典『五大部』,在佛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经以大乘经典的『空观』思想为基础,累积了《阿含》以来的佛陀教义,同时,也强调『无我』的思想与瑜伽的修行等,是中观学派及唯识学派共同尊奉的经典。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