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之记载,见于道安增一阿含经序与诸经录等。但增一阿含经在梁代以后究竟如何,则不得而知。上一节尝言经律异相(五一六)所引十五处增一阿含经中,有十一处可能是引自与今存增一阿含经不同的昙摩难提译之增一阿含经。而其中之一,经推测而知是属于现存杂阿含经之异译单经──鸯崛髻经。如此说来,则昙摩难提译之增一阿含经的别出单经除此经现存外,是否还有其他,就其所译中阿含经有二十四经之别出单经而言,增一阿含经可能尚有别出单经,这同样可一一探索而得。
昙摩难提所译中阿含经有其独特之译语译风,与他人所译有明显之差别,此种现象在增一阿含经亦然,仍以「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始,以「闻佛所说,欢喜奉行」终,关于其独特译语,请参阅下表。而具有其独特风格之经典,在今存大正藏经中,尚可以寻得十八经。兹一一列出如下:
经 名
现存增一阿含相当经
译者名
大正藏所在
1顶生王故事经
〔一七?七经〕
西晋法炬
一?八二二
2.父母恩难报经
〔二○.一一经〕
后汉安世高
一六?七七八
3.八关斋经
〔二四.六经〕
刘宋沮渠京声
一?九一三
4.四人出现世间经
〔二六.五经〕
刘宋求那跋陀罗
二?八三四
5.波斯匿王太后崩尘土坌身经
〔二六.七经〕
西晋法炬
二?五四五
6.婆罗门避死经
〔三一.四经〕
后汉安世高
二?八五四
7.频毗婆罗王诣佛供养经
〔三四.五经〕
西晋法炬
二?八五五
8.长者子六过出家经
〔三五?一○经〕
刘宋慧简
二?八五七
9.鸯崛髻经
〔三八?六经〕
西晋法炬
二?五一○
10.咸水喻经
〔三九?三经〕
西晋失译
一?八一一
11.四未曾有经
〔四二?三经〕
西晋竺法护
二?八五九
12.牧牛经
〔四九.一经〕
姚秦鸠摩罗什
二?五四六
〔四九.一○经〕
13.十一想思念如来经
〔五○.一经〕
刘宋求那跋陀罗
二?八六一
14.四泥犁经
〔五○?五经〕
东晋竺昙无兰
二?八六一
15.阿那邠邸化七子经
〔五一?七经〕
后汉安世高
二?八六二
16.阿难同学经
后汉安世高
?八七四
17.水沫所漂经
东晋竺昙无兰
二?五○一
18.阿闍世王问五逆经
西晋法炬
一四?七七五
上列十八经中,第十三经实由二经合并而成,向来列为增一阿含五十品第一经之一异译经,但另含有与增一阿含第四十九品第十经相当之经,且有「闻如是,一时婆伽婆在……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之一定形式的句子,故知为二经合并而成。此二经于昙摩难提译之增一阿含经为连续之二经,可能因写在同一纸上,故古来被误传为一经。因此,实宜作二经,但今从旧说,仍作一经。
上列十八经中,4、6、7、8、11、13、14、15、16等九经,在今日藏经中,作为增一阿含经之异译单经;5、9、12、17等四经,则作杂阿含经之异译单经;1、3、10三经则为中阿含经之异译本:2、18二经则作阿含经以外之杂经。但今均应改作增一阿含经之异译经,仅最后之16、17、18三经不见有今本增一阿含经之相当经。不过,16阿难同学经系敍女人之五秽行,17水沫所漂经叙五阴(蕴)之譬喻,18阿闍世王问五逆经?五逆罪,均列举五法,故此三经可能是存于昙摩难提所译增一阿含经有关五法中的经。
此十八经,均有译者之名,系据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而译经图纪而开元录,乃至今日藏经之记载而来,是十分不可靠的。据今存最古之经录──僧佑出三藏记集所载,十八经中除水沫所漂经之外,其余十七经皆收入卷四失译杂经录有本部中,故知在梁代(即僧佑当时),十七经已列入译者不明之失译经中。惟出三藏记集所载与十七经经名多少有些出入,如今存鸯崛髻经一经,出三藏记集作央掘髻经,频毘婆罗王诣佛供养经则作频毘婆王诣佛供养经,阿那邠邸化七子经作阿那邠祁化子经,放牛经作牧牛经,十一想思念如来经作十一思惟如来经,或十一相思惟念如来经,咸水喻经作水喻经等略有不同。
至于出三藏记集失译杂经录中所未列出之「水沫所漂经」,其名则见于出三藏记集卷三之安公古异经录中:「河中大聚沫经一卷,或云水沫所漂经,或云聚沫譬经,今有此经。」 (大正五五?一六a)故知水沫所漂经与河中大聚沫经二者可能为彼此相当之经。道安时,在古异经录中明揭河中大聚沫经一名,但至梁代时,另有名为水沫所漂经(至今犹存)之经,僧佑乃以为即是道安古异经录中之河中大聚沫经而视为同经,其实不应混同,水沫所漂经宜列入失译杂经录中。
又在出三藏记集之后的隋法经录、仁寿录,以至唐代之静泰录,皆沿袭此一记载,将此十八经均作为译者不明之失译经;仅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任意安上译者之名,而历经开元录等,沿袭至今,实与史实不符,应将此错误改正为「昙摩难提译」才对。
上列十八经乃具有同一译语译风,与上述经律异相中自增一阿含经所引之十一处(与现存增一阿含经不合者)引文具有类似之译语译风,兹列表比较如下:
经律异相引用之十一处
昙摩难提译之十八经
婆伽婆在
婆伽婆在
舍卫城只树给孤独园
舍卫城只树给孤独园
罗阅只
罗阅只、罗阅城
耆闍崛山
耆闍崛山、灵鹫山
迦兰陀竹园
迦兰陀
波斯匿
波斯匿
舍利弗、目(犍)连
舍利弗、目犍连
沙门、婆罗门
沙门、婆罗门
比丘僧、阿罗汉
比丘僧、阿罗汉
长者、转轮圣王
居士、转轮圣王
三十三天、兜术天
三十三天、兜术天
阎浮提
阎浮里
善处天上
善处天上
恶道
恶道、恶趣
地狱、泥犁
般涅槃
般涅槃
衣被饭食
衣被饮食
病瘦医药、床卧具
病瘦医药、床卧具
结跏趺坐、头面礼足
结跏趺坐、头面礼足
在一面坐、绕三匝
在一面坐、绕三匝
由上表可知,经律异相所引用者,与被推定为昙摩难提译之增一阿含经别生十八经之译语大致相同,故知诸经可能出自昙摩难提所译之增一阿含经。
由上述可知,现存增一阿含经并非昙摩难提所译,而系经僧伽提婆改译者。然则,僧伽提婆于何时何地改译呢?大周刊定录作「隆安元年(三九一)庐山译」(大正五五?四二二a)、开元录亦载「隆安元年正月出,与难提本小异」(大正五五?五○五a)。常盘大定在译经总录(八二八-八三一页)中,认为系在僧伽提婆未至庐山之前,与法和在洛阳时共同改译的。若将僧伽提婆所译增一阿含经与中阿含经之文字加以比较,则可发现虽类似而不尽相同,可能两经之翻译年代与笔受者均不相同。
其中,与昙摩难提所译文字较为相近者,则推增一阿含经,故知增一阿含经之改译时间较中阿含经为早。就此点而言,增一阿含经可能正如常盘所说,以僧伽提婆与法和在洛阳所改译者较为妥当,惟其认为增一阿含经与中阿含之笔受者同属道慈一人乃是错误。总之,僧伽提婆改译增一阿含经之事,在经序中并未提及,且古经录中亦不见有所记载,或因在战乱期间改译而无明确记录所致,今不得而知。
昙摩难提译之增一阿含经与现存僧伽提婆译之增一阿含经二者,在开元录中虽载为「小异」,但大周录所载内容却与现存增一阿含经不同,其中且有现存增一阿含所没有的项目。又被考证为昙摩难提译之增一阿含经之别生单经──现存十八经,其内容与现存增一阿含经中之相当者亦有很大出入,甚至有完全不同者,其中尤其有三经,在现存增一阿含经中找不到相当之经(又经律异相所引用者,有二处在现存增一阿含经中亦找不出相当者),可见此二种增一阿含经绝非出于同一或同类经典,系来自不同部派之经典,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现存增一阿含经之所属部派,法幢在俱舍论稽古中以为系属于大众部。日本明治以后之学者亦多认为属于大众部,但前田慧云则以增一阿含属大众部说之论据薄弱,遂加以否定(详阅大乘佛教史论一六页)。
主张属于大众部派者,如──宇井伯寿,于其「印度哲学研究二?一三七页以下」说:现存增一阿含其列举四阿含之顺序等,与撰集三藏及杂藏传、有部毘奈耶杂事、大智度论等相同,故乍看之下,似属有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其与摩诃僧只律、分别功德论、增一阿含序品等亦有共通之部分,可见其未必属于有部,故应视为属于大众部或其系统所传之阿含。
赤沼智善(佛教经典史论三八页)亦云:「增一阿含在大乘教兴起之后有所增饰,此为明白之事。而就其大乘化及教义之特色来看,乃属于大众部所传。」又松本文三郎认为(佛典之研究三四九页):「增一阿含有二百五十戒,在部派中仅法藏部说二百五十戒,因此可能是属于法藏部之经典。」此说亦颇有道理。赤沼智善亦曾列举法藏部之中与增一阿含共通者五条以强调法藏部说,虽然如此,仍以传自大众部之说较为妥当;大众部有很多部派,增一阿含可能是属于大众部中之说假部所传。(佛教经典史论三九页以下)
关于增一阿含论说得最为详细的,首推平川彰。其主要论点即:增一阿含非属于大众部,其所属部派不明。此说早在日本佛教学会年报(二二号?二五一页)、律藏的研究(四八页)等撰文发表。更在其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中,设「增一阿含非大众部所传」一项加以详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二九~四六页)
在其文中,首先,他声明现存增一阿含经并非如一般所说的为僧伽提婆改译者,他以为应如宇井所说,系出自昙摩难提之手,此由现存增一阿含之内容与道安增一阿含经序相符可知之。又今存增一阿含经之内容含有说一切有部之思想,与法藏部所说吻合之处甚多。在法藏部中具有大乘之说,可由大乘佛教与法藏部具有特殊之关系而知之。平川虽知增一阿含与法藏部、大乘佛教具有密切之关系,但仍认为其所属部派不明。
又现存增一阿含经中,列举十二部经之处有五,但其列举顺序并不一致,此与其他部派之文献所列顺序亦不同,颇为特殊,故难以决定其所属部派。
然则,经考证为昙摩难提译而非现存之增一阿含经,究竟属于何种部派呢?其经数、经典之组织、内容与现在本不同已如上述。而考证两者不同之线索,仅有被考证为昙摩难提译之别生经之一-八关斋经与现存增一阿含经中之有关印度五大河(四大河)之说。
八关斋经所举五大河顺序如下:
恒河Gavgā,谣婆奴Yamunā,新头Sindhū,阿诣耶婆提Aciravatī,摩弃Mahī(大正一?九一三b)。
在巴利佛教、汉译中阿含、有部之法蕴足论、发智论、法藏部之四分律等一般所谓五大河,则去新头而加上萨罗浮Sarabhū,故知八关斋经与一般之五河说多少有些出入。
与八关斋经相当之增一阿含卷二一(二九?九经)、卷三四(四○?一经)未列五大河,仅举出四大河,即恒河Gavgā,新头(私头)Sindhū,私陀(死陀)Sitā,婆叉Vaksā等,与长阿含世记经、大智度论、俱舍论等所说相同。就此而言,则现存增一阿含经所说四大河与法藏部、大乘、说一切有部相似,由此可以推知增一阿含经流行的地域可能为西北印度或西域一带;对此,被认为昙摩难提所译之增一阿含经则表明流行于中部印度一带,因为经中内容不与现存增一阿含相近,而与巴利增支部内容相近。
又就增一阿含经之音译语而言,其原文系有别于梵语、巴利语之佛教梵语的俗语,如六师外道之译语则作:
不兰迦叶 Pūrana,阿夷端 Ajita Kesakambalin,瞿耶楼 Makkhali Gosāla,波休迦旃 Pakudha Kauāyana,先比(毕)卢持Sa?jaya Bela, tthiputta,尼犍子Nigantha Nātaputta。(大正二?七二七c、七六二a以下)
可见其原文系属于极其不同之俗语。其中,波休迦旃之梵语作Kakudha Kātyāyana,或Krakudha K.,不作Pakudha K.。而梵语形系说一切有部之汉译杂阿含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所用,别译杂阿含亦采用之。至于Pakudha K.之形者,乃是巴利佛教、汉译长阿含、中阿含,以及上述增一阿含等之所采用。故知增一阿含亦与有部系不同,可能与法藏部有关系。
又增一阿含有识摩 Ksemā,机梨舍瞿昙弥 Krsā Gotamī 等与梵语形相近者,亦有如质多舍利弗Cittasāriputta、须拔Subhadda、昙摩提那 Dhammadinnā 等与巴利语形接近者,但亦有如波罗遮那Patācārā(sk. p. )一词,既非梵语亦非巴利语者。
汉译经典中,有后汉安世高所译七处三观经,内容由四十七经组成,为一经典群。此经即在七处三观经原经,与积骨经、九横经等三经之外,再加上四十四经而构成者;本为各个别行之经,但因与七处三观经放在一起,故现在合称为七处三观经。其最初二经属于杂阿含,后之四十四经即为道安录(出三藏记集)所说安世高译之杂经四十四篇。此四十四经为增一阿含之一种,系由敍说二法者十经,说三法者五经,四法者十四经,五法者十三经,说六法乃至八法者一经,说九法者一经所组成的,这是缺少说一法之经,且六法以下亦见有错杂简略之不完全的经典。总之,原系增一阿含之抄本,可能为流行于安息国之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又与增一阿含之抄本相近者,有汉译之本事经与巴利之如是语经。但如是语经(Itivuttaka,本事经Itivrttaka)之经首并非「如是我闻」,而是以「吾从世尊闻如是语Vuttam hetam bhagavatā vuttam arahatā ti mesutam」之一定形式的句子开始,经末并不以「闻佛所说,欢喜奉行」结束,故以经典形式而言与增一阿含的形式完全不同,但所收集之经典的内容、种类与增一阿含共通者颇多。又此二经典之纂辑方式,亦与增一阿含相同。如本事经(大正一七?六六二)包含有一法六○经、二法五○经、三法二八经,计一三八经,而巴利小部之如是语经则包含有一法二七经、二法二二经、三法五○经、四法一三经,计一一二经,并与上文杂经四十四篇有类似之点。
国译增一阿含经解题(一)中曾言别译增一阿含经之单经有二十三经,但实际上,现在被作为别译杂阿含、中阿含之别译,或作为阿含经以外之单经而应被视为别译增一阿含经者,有数十经之多(包括杂经四十四篇),凡此已如上述。而此增一阿含经之别译经中,有正确标上译者之名者,亦有随便按上译者、译出年代者,此一问题则应重新做学术上之检讨。
注:文中所引用之参考质料,除上述外,另有下列资料:
林屋友次郎「安世高译の杂阿含と增一阿含」 (佛教研究一ノ二?三七~五○页)
水野弘元「汉译中阿含の增一阿含の译出につぃて」(大山学院纪要第二辑四一~九○页)
前田惠学「原始佛教の成立史研究」六六三~六七三页。
在上文中,虽将现存汉译增一阿含经从众说,作为僧伽提婆译,但亦可如宇井、平川之说,将今存增一阿含经视为昙摩难提译,且以道安增一阿含经序所载经典之数、组织与现存增一阿含经吻合作为有力之证据;同时,大周录、宝唱录所列僧伽提婆译之增一阿含经,其组织、内容与现存增一阿含经并不一致,亦如前文所言:因此,若相信此二经录之记载,则亦可作为今本增一阿含非僧伽提婆所译之佐证。
如此说来,则现存增一阿含经并非僧伽提婆(第二译)所译,而为昙摩难提译(第一译),则上述中所推定为昙摩难提译之十八经,与经律异相所引增一阿含十一处之文,即是僧伽提婆所译。而今日失传之增一阿含经则含有现存增一阿含经所缺之经典,故比较起来可能比今本增一阿含经多出八十经以上,大约有五五五经。
若是上述推论与史实相符,则汉译中阿含亦可作同样之推论。在中阿含,现存本亦为僧伽提婆译(第二译(,而昙摩难提译(第一译)则为失传者,仅有别行二十四经因系单译而流传至今。此于「中阿含解题」(补遗)中即已推定为昙摩难提译。但若就上述推论而言,则现存中阿含应作为昙摩难提译,二十四单行经应作为僧伽提婆译。盖中阿含单本二十四经与考证为增一阿含之别行单本十八经具有共同译语、译风等特徵,则应系同属一译者,即同为僧伽提婆所译。
换言之,若仅将现存增一阿含经作为昙摩难提译,而中阿含仍作为僧伽提婆译,则今日业已亡佚之增一阿含变为僧伽提婆译,亡佚之中阿含仍为昙摩难提译,就不甚妥当!因为失佚之中阿含与增一阿含,就其残存之经典而言,可以看出二者系同出于一译者之手,故关于此一问题有待后之学者作进一步之考证。(日本国译一切经第四册)

杂阿含经白话译解

增一阿含经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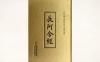
长阿含经新译

杂阿含经新译

增一阿含经白话文

中阿含经新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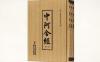
中阿含经原文

对于人类的起源学者有学者的解释,其他宗教也有各自的记载。但是佛教中对于人类的起源有不同的讲述。在《长阿含经》中释伽牟尼佛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天地始终。劫尽坏时。众生命终皆生光音天。自然化生。以念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空。其后此地尽变为水。无不周遍。当于尔时。无复日月星辰。亦无昼夜年月岁数。唯有大冥。其后此水变成大地。

无我法门是佛教中重要的教义,被列为三法印之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在佛教中,判断佛法是否究竟,即以此三法印来衡量。若是与三法印相违,即使是佛亲口所说,也不是了义之法;反之,若能契合三法印,即使不是佛陀所说,也可认为是纯正的佛法。因此,对于学佛者来说,正确地把握三法印的含义,对整个修行来说是极为关键的。本文

我是这样听说的:一天,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与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们一起。那时,摩竭王阿阇世准备讨伐跋祇。摩竭王自我念道:‘跋祇勇猛健壮,民众也豪强。以我的实力去赢取他们,不一定有十足的胜算。’阿阇世王,即命令婆罗门种族大

阿含,梵语音译,也作阿铪、阿笈摩、阿伽摩、阿鋡暮。意译为“无比法”、“法归”、“教”“传”等。《阿含经》记述佛陀所说及其直传弟子依次所为的修道及传教活动,阐述当时“外道”的学说以及佛陀对他们的批驳。论述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包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缘

过去,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礼多人不怪」,也经常看到许多信徒欢喜礼拜,表达他的信仰恭敬、虔诚。这原本也是没有错,但是不如法的礼拜,也是不当的。经文里说,「偷婆」(即窣堵波,梵语 stúpa 音译,安置佛陀舍利的建筑)中不应拜,也就是在塔里不拜;在大众里

原始佛教时代,佛弟子及信者往往将所听闻的教法,用诗或简短散文的形式,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记忆传承。由于佛弟子各人领纳的不同,而各有其相异的思想,因此至教团成立时,如何将佛陀的教说作整理、统一,实属必要之事。经过历次的结集后,佛陀的教说渐次充实完备,

阿含,梵文Agama,巴利语同,又作阿笈摩、阿伽摩、阿铪暮、阿铪等。汉译意为法本、净教、归、法归、法藏、藏、教法、传教、趣无、教、传、来。阿含一词,意指传承之教说,或传承佛陀教法之圣典;有时与法(梵文dharma)同义。称阿含为《阿含经》乃是中国古来之习惯,通常系指原始佛教典籍《四阿含》或《五阿含》而言。

以瞋报瞋者,是则为恶人;不以瞋报瞋,不瞋胜于瞋。这四句偈提醒我们,对于瞋恨心重的人,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也不要瞋心以对。例如,对方瞋恨人,辱骂人,你也以瞋心骂他;这个人很罪恶,你也以一颗瞋恨心对待他,这都是不当的。如果能以慈悲心、忍辱心,以一颗不瞋恨的心来面对,就是可以的人。

世间的实相真理是什么?是无常!你看,人有生老病死,花有花开花谢,大地山河无时无刻不在迁流变化中。无常,就是有变异性,没有一刻停留不变。尤其人的生命也是无常,有人做了实验,发现人身上的细胞,只要一个礼拜就会全部死亡,重新

在社会上,常有人习惯对人发脾气、叫嚣谩骂,令人不敢领教。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战胜瞋恚心重的人呢?这首偈语告诉我们「不怒胜瞋恚」,对于瞋心重的人,要以和平、慈悲、温和,不跟他一般见识、不计较来回应,即所谓「柔能克刚」,就能战胜他心中的愤怒。

《中阿含经》由东晋瞿昙僧伽提婆翻译,共六十卷,一共包括了二百二十二部经典。由于这些经典在《阿含经》中篇幅中等,故名《中阿含经》。其内容有多个方面:(1)论述戒定等各种修行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解脱过程中的作用;(2)论述因果报应;(3)论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佛教基本教义。汉译《中阿含经》一般认为是说一

《杂阿含经》由南朝宋求那跋陀罗翻译,共五十卷,收入篇幅较短的佛经一千三百六十二部,内容广^泛杂乱,故称《杂阿含经》。《杂阿含经》的主要内容以讲述佛教基本教义为主,详细解释了五蕴、六处、缘起、十二缘生等学说,阐明了苦、空无常、无我的佛教基本思想,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四谛、八正道、四念处、十八界、因果报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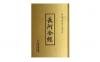
汉文《长阿含经》是由后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共同译定的,计二十二卷,它由十部不同体裁的经典汇集而成。由于所收经典在全部《阿含经》中属篇幅较长的,故被称为《长阿含经》。《长阿含经》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表述佛教基本教义。它把佛教的基本概念以数字先后为顺序进行排列,进行叙述和表达。主要内容包括四谛、八正道、十二

《大般若经》六百卷,又称《般若经》,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朝玄奘翻译。这是有关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之著,所以卷帙浩繁。当年玄奘法师西域取经,取来此经本子有三种,后来进行翻译,碰到疑问,便就三本互校,殷勤省覆,择善而从,然后落笔,

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基本经典之一。唐玄奘译。五卷。除玄奘译本外,还有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北魏菩提流支、南朝陈真谛译的三种译本。该经的中心,是大乘的境行果,境指心境。一共八章,即:序、胜义谛相、心意相识、一切法相、无自性相、分别瑜伽、地波罗蜜、如来成所事。除序外,其余七章(品)是正文。正文前四章,讲“所观境”;中间二

布施有很大的功德,但布施若没有智慧或布施错误,就会有过失。例如:拿钱给小孩买刀剑玩具,玩惯以后,他可能会用真刀真剑去伤害人;买小鱼、小鸟给小孩子玩,一直玩到死,养成没有慈悲心,这也不好。买香菸送人、买酒送人、替人传递毒品、捕鸟送人、捕鱼送人、

什么叫「居家善知识」?家里的成员中,可以作为模范者,他就是家庭里的善知识;做先生的,因为太太的支持而有成就,太太就是先生的善知识;贞节贤良的妻子,是我们居家的善知识;具有正见智慧的老师,是学校的善知识;从事社会公益的好人,是社会的善知识。

有人说,世间上,花种中最美丽的是玫瑰花;鸟类中最美丽的是孔雀;动物中最忠实的是狗;至于人的一生,在物质上,最重要的是土地房屋;在精神上,最重要的是有伴侣;在生活上,最重要的是衣食不缺……但,什么是人的真正第一呢?梦窗国师有一首偈语:

经文中,佛陀提到布施有五种:第一施命:永明延寿禅师出家前是一位太守,生性慈悲,为了护生挪用公款,被判罪要砍头。他在被杀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将此一命,布施众生。」过去的圣贤豪杰「杀生成仁,捨身取义」,都是一命来布施;现在有很多人,用自己

在平常生活中,我们的身心是快乐呢﹖还是痛苦呢﹖有的人觉得自己身体健康,只是烦恼很多,不能心生欢喜;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内心自在,只是身体上有种种的病苦。世间本来就是苦乐参半,如何去除苦因,只存安乐与自在呢?这就必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观自在;观照自己很

经文中指出,宁可毁坏六根,也不造作诸恶,而堕入三恶道。因为六根有贪著的病,就会在生死轮迴的苦海中不断流转,故必须注重六根的修行。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称做「六根」,属生理的,又叫作「六色」,六根遇到外面属于物理的「六尘」(色尘、身尘、香

有人问:「佛陀会不会骂人呢﹖」佛陀不是在骂人,佛陀会教训那些愚痴的人。如:「你不知惭愧」、「你不知道苦恼」、「你愚痴」等。还有一句比较严重的话:「你是非人!」非人,就是不像个人,也就是说「你不是人」,即是邪见的邪人,不正派的人。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责

《杂阿含经》卷四中说:“如是烦恼漏,一切我已舍,已破已磨灭,如芬陀利生,虽生于水中,而未曾着水。”意思是说,这样的烦恼等有漏,一切我都已经舍弃了,已磨灭了,已破坏了,就好像芬陀利花,虽然在水中生长,而没有染着于水。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