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五迁,将治亳殷,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盘庚治亳殷。○盘,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忧愁,相与怨上。○胥,徐思馀反。怨,纡万反。作《盘庚》三篇。
[疏]“盘庚”至“三篇”○正义曰:商自成汤以来屡迁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诰,历载於篇。盘庚最在其后,故序总之,“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今盘庚将欲迁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恋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忧愁,相与怨上,盘庚以言辞诰之。史叙其事,作《盘庚》三篇。○传“自汤”至“亳怨”○正义曰:经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盘庚五迁”。传嫌一身五迁,故辨之云“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并数汤为八,此言“盘庚五迁”,又并数汤为五,汤一人再数,故班固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实正十二也。”此序云盘庚“将治亳殷”,下传云“殷,亳之别名”,则“亳殷”即是一都,汤迁还从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束晳云:“《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旧说以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书》云‘将始宅殷\\’,是与古文不同也。《汉书·项羽传》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阳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与亳异也。然孔子壁内之书,安国先得其本,此“将治亳殷”不可作“将始宅殷”。“亳”字摩灭,容或为“宅”。壁内之书,安国先得,“始”皆作“乱”,其字与“始”不类,无缘误作“始”字,知束晳不见壁内之书,妄为说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当馀王居之,非盘庚也。盘庚治於亳殷,纣灭在於朝歌,则盘庚以后迁於河北,盖盘庚后王有从河有亳地迁於洹水之南,后又迁于朝歌。○传“胥相”至“怨上”○正义曰:《释诂》云:“胥,皆也。”“相”亦是皆义,故通训“胥”为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忧愁,相与怨上,经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迁都,序无民怨之言,此独有怨者,盘庚,祖乙之曾孙也,祖乙迁都於此,至今多历年世,民居已久,恋旧情深;前王三徙,诰令则行,晓喻之易,故无此言;此则民怨之深,故序独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独三篇者,谓民怨上,故劝诱之难也。民不欲迁,而盘庚必迁者,郑玄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圮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乐徙。”王肃云:“自祖乙五世至盘庚,元兄阳甲,宫室奢侈,下民邑居垫隘,水泉泻卤,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谧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来,民皆奢侈,故盘庚迁於殷。”此三者之说皆言奢侈,郑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肃专谓君奢,皇甫谧专谓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宫室奢侈,侵夺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过度,逼迫贫乏;皆为细民弱劣无所容居,欲迁都改制以宽之。富民恋旧,故违上意,不欲迁也。案检孔传无奢侈之语,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传云:“水泉沈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定之极,徙以为之极。”孔意盖以地势洿下,又久居水变,水泉泻卤,不可行化,故欲迁都,不必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为君时事,而郑玄以为上篇是盘庚为臣时事,何得专辄谬妄也!
盘庚盘庚,殷王名。殷质,以名篇。○盘庚,殷王名。马云:“祖乙曾孙,祖丁之子。不言‘盘庚诰\\’何?非但录其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盘庚”名篇。
[疏]“盘庚”○正义曰:此三篇皆以民不乐迁,开解民意,告以不迁之害,迁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迁时事,下篇既迁后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启民心,故其辞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辞稍缓。下篇民既从迁,故辞复益缓。哀十一年《左传》引此篇云“盘庚之诰”,则此篇皆诰辞也。题篇不曰“盘庚诰”者,王肃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盘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则是史意异耳,未必见他义。○传“殷质,以名篇”○正义曰:《周书》谥法成王时作,故桓六年《左传》云:“周人以讳事神。”殷时质,未讳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传者,以上篇经亡,此经称《盘庚》,故就此解之。《史记·殷本纪》云:“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与此序违,非也。郑玄云:“盘庚,汤十世孙,祖乙之曾孙,以五迁继汤,篇次《祖乙》,故继之。于上累之,祖乙为汤玄孙,七世也,又加祖乙,复其祖父,通盘庚,故十世。”《本纪》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开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门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阳甲立。崩,弟盘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盘庚,故为曾孙。
盘庚迁于殷,亳之别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率吁众慼,出矢言,吁,和也。率和众忧之人,出正直之言。○吁音喻。慼,千历反。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无尽刘。刘,杀也。所以迁此,重我民,无欲尽杀故。○尽,子忍反。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则当卜稽於龟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先王有所服行,敬谨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迁辄迁。○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汤迁亳,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国都。○马云:“五邦谓商丘、亳、嚣、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今不承古而徙,是无知天将断绝汝命。○断又音短。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天将绝命,尚无知之,况能从先王之业乎?○从,才容反。若颠木之有由蘖,言今往迁都,更求昌盛,如颠仆之木,有用生蘖哉。○蘖,五达反,本又作枿,马云:“颠木而肄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言天其长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言我徙欲如此。○厎之履反。
[疏]“盘庚”至“四方”○正义曰:盘庚欲迁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别有邑居,莫不忧愁,相与怨上。盘庚率领和谐其众忧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晓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从旧都来,於是宅於此地。所以迁於此者,为重我民,无欲尽杀故。先王以久居垫隘,不迁则死,见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谋而来徙。以徙为善,未敢专决,又考卜於龟以徙。既获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汤以来,凡有所服行,敬顺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则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则是无知天将断绝汝命矣。天将绝命,尚不能知,况曰其能从先王之基业乎?今我往迁都,更求昌盛,若颠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犹木死生蘖哉。我今迁向新都,上天其必长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继复先王之大业,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原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则天将绝汝命,谓绝臣民之命,明亦绝我殷王之命。复云若迁往新都,天其长我殷之王命,明亦长臣民之命,互文也。○传“亳之别名”○正义曰:此序先“亳”后“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内之别名。郑玄云:“商家自徙此而号曰殷。”郑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将迁於殷,先正其号,明知於此号为殷也。虽兼号为殷,而商名不改,或称商,或称殷,又有兼称殷商。《商颂》云“商邑翼翼”、“挞彼殷武”是单称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称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谓之亳社,其亳郑玄以为偃师,皇甫谧以为梁国穀熟县,或云济阴亳县。说既不同,未知谁是。○传“適之”至“邑居”○正义曰:《释诂》云:“適、之,往也。”俱训为往,故“適”得为之,不欲往彼殷地,别有新邑居也。○传“吁和”至“之言”○正义曰:“吁”即裕也,是宽裕,故为和也。忧则不和,“慼”训忧也,故“率和众忧之人,出正直之言”。《诗》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为“正直之言”。○传“我王”至“於此”○正义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地,迁都於耿,今盘庚自耿迁于殷,以“我王”为祖乙,此谓耿也。○传“刘杀”至“杀故”○正义曰:“刘,杀”,《释诂》文。水泉咸卤,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杀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迁此者,重我民,无欲尽杀故也。○传“言民”至“所行”○正义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谓水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义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龟以徙,《周礼·大卜》:“大迁考贞龟。”是迁必卜也。○传“先王”至“辄迁”○正义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汤以来数之,则此言“先王”总谓成汤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谓行有典法,言能敬顺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盘庚言先王敬顺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迁辄迁;况我不能敬顺天命,不迁民必死矣,故不可不迁也。○传“汤迁”至“国都”○正义曰:孔以盘庚意在必迁,故通数“我往居亳”为“五邦”。郑、王皆云,汤自商徙亳,数商、亳、嚣、相、耿为五。计汤既迁亳,始建王业,此言先王迁都,不得远数居亳之前充此数也。○传“言今”至“蘖哉”○正义曰:《释诂》云:“枿,馀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馀也。”郭璞云:“晋卫之间曰枿。”是言木死颠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毁坏,若枯死之木,若弃去毁坏之邑,更得昌盛,犹颠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敩,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敩,户教反,下如字。度如字。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无有故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戒朝臣。○箴,之林反,马云:“谏也。”朝,直遥反。
[疏]“盘庚”至“攸箴”○正义曰:前既略言迁意,今复并戒臣民。盘庚先教於民云:“汝等当用汝在位之命,用旧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从其臣言也。民从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无有敢伏绝小人之所欲箴规上者。”○传“敩教”至“朝臣”○正义曰:《文王世子》云:“小乐正敩干,大胥赞之。籥师敩戈,籥师丞赞之。”彼并是教舞干戈,知“敩”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规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绝之。郑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将属民而询焉,故敕以无伏之。”
王命众悉至于庭。众,群臣以下。
[疏]传“众,群臣以下”○正义曰:《周礼》:“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是国将大迁,必询及於万民。故知众悉至王庭是“群臣以下”,谓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劝民,故以下多是责臣之辞。
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谋退汝违上之心,无傲慢,从心所安。○傲,五报反。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先王谋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鸩反。
[疏]传“先王”○正义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无指斥者,皆谓成汤已来诸贤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谓汤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谓迁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谓先世贤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钦”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饿反。匿,女力反。
[疏]传“王布”至“其指”○正义曰:上句言先王用旧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当谓告臣耳。传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变”,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王用大敬其政教,无有逸豫之言,民用大变从化。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聒聒,无知之貌。起信险伪肤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讼言何谓。○聒,古活反,马云《说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
[疏]传“聒聒”至“何谓”○正义曰:郑玄云:“聒读如‘聒耳\\’之聒,聒聒,难告之貌。”王肃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传以“聒聒”为“无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乱人之意也。“起信险肤”者,言发起所行,专信此险伪肤受浅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争讼,我不知汝所讼言何谓。言无理也。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我之欲徙,非废此德。汝不从我命,所含恶德,但不畏惧我耳。我视汝情如视火。○惕,他历反。
[疏]“非予”至“观火”○正义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变。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废此丕钦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恶,不畏惧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谓我不知。我见汝情若观火。言见之分明如见火也。
予亦拙谋,作乃逸。逸,过也。我不威胁汝徙,是我拙谋成汝过。○拙,之劣反。
[疏]传“逸过”至“汝过”○正义曰:“逸,过”,《释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迁,则无违上之过也。我不威胁汝徙,乃是我亦拙谋,作成汝过也。恨民以恩导之而不从己也。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紊,乱也。穑,耕稼也。下之顺上,当如网在纲,各有条理而不乱也。农勤穑则有秋,下承上则有福。○紊音问,徐音文。
[疏]传“紊乱”至“有福”○正义曰:“紊”是丝乱,故为乱也。“稼”、“穑”相对,则种之曰“稼”,敛之曰“穑”。“穑”是秋收之名,得为耕获总称,故云“穑,耕稼”。“下承上则有福”,“福”谓禄赏。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汝群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实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则我大乃敢言汝有积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昬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昬,强。越,於也。言不欲徙,则是不畏大毒於远近。如怠惰之农,苟自安逸,不强作劳於田亩,则黍稷无所有。○昬,马同;本或作暋,音敏。《尔雅》昬、暋皆训强,故两存。越,本又作粤,音曰,于也。强,其丈反。
[疏]传“戎大”至“所有”○正义曰:“戎,大”、“昬,强”、“越,於”皆《释诂》文。孙炎曰:“昬,夙夜之强也。《书》曰:‘不昬作劳。’”引此解彼,是亦读此为昬也。郑玄读“昬”为暋,训为勉也,与孔不同。传云“言不欲徙,则是不畏大毒於远近”,其意言不徙则有毒,“毒”为祸患也;“远近”谓赊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强於作劳,则黍稷无所获,以喻不迁於新邑,则福禄无所有也。此经惰农弗昬无黍稷,对上“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详略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责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
[疏]传“责公”至“毒害”○正义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独云“百姓”,则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经是责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乐迁也。不和百官,必将遇祸,是公卿自生毒害。
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为败祸奸宄以自灾之道。○宄音轨。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群臣不欲徙,是先恶於民。恫,痛也。不徙则祸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则於身无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恫,敕动反,又音通,痛也。
[疏]传“群臣”至“所及”○正义曰:群臣是民之师长,当倡民为善,群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恶於民也。“恫,痛”,《释言》文。
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言憸利小民,尚相顾於箴诲,恐其发动有过口之患,况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从我,是不若小民。○相时,相,息亮反,马云:“视也。”徐息羊反。憸,息廉反,马云:“憸利,小小见事之人也。”徐七渐反。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曷,何也。责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徙,恐汝沉溺於众,有祸害。○曷,何末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火炎不可向近,尚可扑灭。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得遏绝之。○燎,力召反,又力鸟反,又力绍反。向,许亮反。扑,普卜反。近,附近之近。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谋也。是汝自为非谋所致。
[疏]“相时”至“有咎”○正义曰:又责大臣不相教迁徙,是不如小民。我视彼憸利小民,犹尚相顾於箴规之言,恐其发举有过口之患,故以言相规。患之小者尚知畏避,况我为天子制汝短长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从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不以情告我,而辄相恐动以浮华之言?乃语民云:“国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沉溺於众人,而身被刑戮之祸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炽不可向近,其犹可扑之使灭,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绝也。若以刑戮加汝,则是汝众自为非谋所致此耳,非我有咎过也。○传“曷何”至“祸害”○正义曰:“曷”、“何”同音,故“曷”为何也。顾氏云:“汝以浮云恐动不徙,更是无益。我恐汝自取沉溺於众人,不免祸害也。”○传“我刑”至“所致”○正义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谋”,《释诂》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谋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为非谋所致也。
“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遟任,古贤。言人贵旧,器贵新,汝不徙,是不贵旧。○遟,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马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言古之君臣相与同劳逸,子孙所宜法之,我岂敢动用非常之罚胁汝乎?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选,数也。言我世世数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选,息转反,又苏管反。掩,本又作弇。数,色主反。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古者天子录功臣配食於庙。大享,烝尝也。所以不掩汝善。○与音预。烝,之丞反。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善自作福,恶自作灾,我不敢动用非罚加汝,非德赏汝乎?从汝善恶而报之。
[疏]“遟任”至“非德”○正义曰:可迁则迁,是先王旧法。古之贤人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言人贵旧,器贵新,汝不欲徙,是不贵旧,反遟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与同逸豫,同勤劳,汝为人子孙,宜法汝父祖,当与我同其劳逸。我岂敢动用非常之罚胁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数汝功劳,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从我先王与在宗庙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恶自作灾,我亦不敢动用非德之赏妄赏汝,各从汝善恶而报之耳。其意告臣言从上必有赏,违命必有罚也。○传“遟任”至“贵旧”○正义曰:其人既没,其言立於后世,知是古贤人也。郑玄云:“古之贤史。”王肃云:“古老成人。”皆谓贤也。○传“选数”至“於汝”○正义曰:《释诂》云:“算,数也。”舍人曰:“释数之曰算。”“选”即算也,故训为数。经言世世数汝功劳,是从先王至己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责臣之不忠也。○传“古者”至“汝善”○正义曰:《周礼·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谓天子祭宗庙也。传解天子祭庙,得有臣祖与享之意,言“古者天子录功臣配食於庙”,故臣之先祖得与享之也。“古者”孔氏据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时已然矣。“大享,烝尝”者,烝尝是秋冬祭名,谓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对。若烝尝对禘祫,则禘祫为大,烝尝为小。若四时自相对,则烝尝为大,礿祠为小。以秋冬物成,可荐者众,故烝学为大;春夏物未成,可荐者少,故禘祫为小也。知烝尝有功臣与祭者,案《周礼·司勋》云“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勋诏之”是也。尝是烝之类,而传以尝配之,《鲁颂》曰“秋而载尝”是也。《祭统》云“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外祭则郊社是也”。然彼以祫为大尝,知此不以烝尝时为禘祫,而直据时祭者,以殷祫於三时,非独烝尝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则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末成故也。近代已来,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时祭不及之也。近代已来,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庙已毁,时祭不祭毁庙,其君尚不时祭,其臣固当止矣。禘祫则毁庙之主亦在焉,其时功臣亦当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时祭,其夏秋冬既为祫,又为时祭。诸侯亦春为时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时祭,而后祫。周则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传》云:“五年再殷祭。”《礼纬》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郑氏之义,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难,当如射之有所准志,必中所志乃善。○射,食夜反。准音准。中,丁仲反。
[疏]“予告”至“有志”○正义曰:既言作福作灾由人行有善恶,故复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难,犹如射之有所准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为善耳。”以喻人将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为善耳。其意言迁都是善道,当念从我言也。○传“告汝”至“乃善”○正义曰:此传惟顺经文,不言喻意。郑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难矣。夫射者,张弓属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后发之。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后出之。”
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徙则孤幼受害,是弱易之。○侮,亡甫反。易,以豉反。
[疏]传“不用”至“易之”○正义曰:“老”谓见其年老,谓其无所复知。“弱”谓见其幼弱,谓其未有所识。郑云:“老弱皆轻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则水泉咸卤,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则是卑弱轻易之也。
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盘庚群臣下各思长於其居,勉尽心出力,听从迁徙之谋。○长,丁丈反。
[疏]传“盘庚”至“之谋”○正义曰:於时群臣难毁其居宅,惟见目前之利,不思长久之计。其臣非一,共为此心。盘庚群臣下各思长久於其居处,勉强尽心出力,听从我迁徙之谋。自此已下皆是也。
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远近待之如一,罪以惩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劝慕,竞为善。○去,起吕反。
[疏]“无有”至“厥善”○正义曰:此即迁徙之谋也。言我至新都,抚养在下,无有远之与近,必当待之如一。用刑杀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过,罪以惩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树然,言止而不复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赏禄以明之,使竞慕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对,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赏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赏善,死是刑之重者,举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赏,故言“彰厥善”;行赏是德,故以“德”言赏;人生是常,无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众。有善则群臣之功。○臧,徐子郎反。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罚。罪己之义。○佚音逸。凡尔众,其惟致告:致我诚,告汝众。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奉其职事,正齐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渡。
[疏]“度乃口”○正义曰:“度”,法度也,故传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罚及尔身,弗可悔。”不从我谋,罚及汝身,虽悔可及乎?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翻译:孔子说:学习并时常温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从心里感到高兴吗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知止(4)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孔子说:学习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是件高兴的事吗?有好朋友从远方来(互相切磋,增长学问),不是件快乐的事吗?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怨恨别人,不也是有道德的表现吗? 2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翻译】孔子说:“学习了知识又时常实践,不也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知道)我,我却不怨恨(生气)

夫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战国初兴,至化陵迟,异端并作,仪、衍肆其诡辩,杨、墨饰其淫辞。遂致王公纳其谋,以纷乱於上;学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犹洚水怀山,时尽昏垫,繁芜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

《礼记正义》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汉代有郑玄作注,唐代有孔颖达为之正义,都是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阅读研究《礼记》的重要版本。今归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由吕友仁先生拟影印宋绍熙刻本《礼记正义》校以

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又称论语注疏解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二十卷。案何注皇疏皆以道家思想解论语,又於名物制度无所考订,颇为学人所不满。北宋时遂由朝廷於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昺删除皇疏之文,而归向儒学本来之义理,又加名物制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春秋左氏》,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左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

谦受益,满招损,谦虚纳百福。成功的人物没有不谦虚的,不谦虚就会很快失败。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而拜,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谦虚得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呵护,就连鬼神都呵护它。“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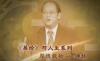
坤卦是八卦中至柔至顺的一卦。由六个阴爻组成,底部三个阴爻为下坤卦,上面三个阴爻为上坤卦。由下到上依次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坤卦的卦辞:元、亨、利牝(bi母)马贞。用母代表坤卦,用马代表健行,有恒心。每一个人都有阴性的魂和阳性的魂。

第四讲:自强不息——乾卦,乾卦是天下第一卦,代表生命的开始。乾卦由由下到上六条横线组成,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一到九的奇数代表阳,偶数代表阴,九最大代表无穷的力量,六居中代表安静。在古代,龙是三栖动物。

第三讲:八卦的卦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相互转化。“女子虽弱,为母则强”。八个卦象的写法: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巽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第二讲:《易经》的由来,易经的发展三位圣人:伏羲氏、周文王和孔子做了巨大的贡献。开天辟地之后,人要怎样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和发展,让伏羲氏产生了忧患意识,易经起源于忧患。易经的核心是居安思危。伏羲氏抬头观天象,观察天体的运转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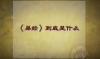
第一讲:《易经》是什么?易经是“不学不会,学了不一定会,会来终身受用”。易经的重点是修德行善。易经包括义理和象数。义理指为人处事的道理;象数指卦象的计算规律。易经是“观天道立人道”,真正的儒家是由内而发,西方有哲学派别认为“人是唯一使用符号的动物”。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lè)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学而》) 2 曾子曰:吾(wú)日三省(xǐng)吾(wú)身,

一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

[问]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生异类,本为养人。禁之宰杀,逆天甚矣。[答]既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奈何不知万物为天地之赤子。赤子之中,强凌弱,贵欺贱,父母亦大不乐矣。倘因食其肉,遂谓天所以养我,则虎、豹、蚊、虻,亦食人类血肉,将天之生人

不管《三字经》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在有限篇幅当中赞扬了两位非常有才学的女子,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蔡文姬,而另一位是我们比较陌生的谢道韫。谢道韫是东晋时期著名才女,我们知道有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之家和寻常百姓之家是对着

大家都知道,人最好是从岁数很小时,就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就开始勤奋地学习,就开始接受良师的指导。但人世间的很多事是难以预料的。很多人或说更多的人,因种种原因错过了最佳的读书和受教育年龄。那年岁大的人还应不应学习?年岁大的人学习了还能不能够取

学习离不开刻苦的精神,《三字经》对这点当然不会放过,它也非常强调,所以《三字经》用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稍微有点那么极端的故事,来张扬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我们后来把这两个故事并成一个成语叫悬梁刺

三字经一直是通过讲故事,把一些深刻的道理,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既然是讲学习,谁最合适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谁是一个学习的楷模呢?毫无疑问是孔子。所以接下来三字经讲:昔仲尼,师项橐(驼)。古圣贤,尚勤学。字面意思非常清楚,想当年孔老夫子拜项橐为师

接下来,《三字经》又用12个字讲述了明朝的败亡。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也就是说永乐帝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到了崇祯就在煤山去世,这位皇帝在人世间活了只不过33岁,他是1611年出生,1644年在煤山上吊自杀,不少人认为,崇祯实在并不是一个坏皇

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明太祖,久亲师的故事,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长时间的亲自率领军队进行征战,最后成功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明朝,那么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他是用哪些手段、方法、理念,换句话说,他是怎样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是高度集

根据我所采用的这个版本,元朝以后的明朝是《三字经》讲述的最后一个朝代。一般认为讲述到后来的清朝乃至民国都是后来比较近的人离今天比较近的人增补的所以我们讲《三字经》,在历史部分就讲到明朝。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这样四句12个字是讲述了明太

在中国历史上接着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的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就是元朝,三字经讲元朝时是这么讲的: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并中国,兼戎翟。什么意思呢?到了元朝兴起时金朝也灭亡了,因为金朝是被元朝和南宋联合灭亡的。有宋氏 一同灭,连宋朝捎带着也灭亡了

赵匡胤即位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抗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皇帝的位子还没坐暖呢就御驾亲征,费了不小的劲才把这两个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镇压下去,这件事使赵匡胤心里怎么都不踏实,所以有一天他就单独召见赵普这位自己主要的谋士,跟他商量。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