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从事,谓修荐可以祭者也。
[疏]“君子”至“尽也”。○正义曰:此一节申明反古复始、竭力报亲之事。○“是以致其敬,发其情”者,以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故致其恭敬,发其情性,竭力从事,以报其亲。谓竭尽气力,随从其事,以上报其亲,不敢不极尽也。
“是故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先古,先祖。○藉,在亦反。藉田,《说文》作耤。纮音宏。耒,方内反。酪音洛。齐音咨,本亦作齐。
[疏]“是故”至“至也”。○正义曰:以君子报亲,不敢不尽心以事之,故古天子、诸侯有藉田以亲耕。○“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者,上虽总论天子、诸侯,此言天地者,特据天子,自外则通。先古,谓先祖也。“以为醴酪齐盛於是乎取之”者,为祭祀诸神须醴酪粢盛之属,於是乎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牺、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君皮弁素积,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谓将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视之,君召牛,纳而视之,更本择牲意。○朝,直遥反,注“躬朝”同。牷音全。
[疏]“古者”至“至也”。○正义曰:此一经明孝子报亲,竭力养牲之事。“及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者,云“岁时”,谓每岁依时,谓朔月、月半也。躬,亲也。既卜牲,吉,在牢养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辞也。○“牺、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者,牺,纯色,谓天子牲也;牷,完也,谓诸侯牲也。牺、牷,所祭之牲,必於是养兽之官受择取之。养兽者,若《周礼》牧人也。○“君召牛,纳而视之”者,此更本择牲之时,君於牧处,更命取牛,采纳之於内而视之。○“君皮弁素积,朔月、月半君巡牲”者,即前言岁时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诸侯视朔之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者,是孝道之至极。耕藉云“敬之至”,养牲云“孝之至”,互文也。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诸侯夫人三宫,半王后也。风戾之者,及早凉脆采之,风戾之使露气燥,乃以食蚕,蚕性恶湿。○近,附近之近。仞音刃,七尺曰仞。昕,许斤反,日欲出。蚕,才南反。奉,芳勇反,下及注同。种,章勇反。戾,力计反,燥也。食音嗣。蚤音皂,本亦作早。脆,七岁反。燥,悉皂反。恶,乌路反。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岁单,谓三月月尽之后也。言岁者,蚕,岁之大功,事毕於此也。副、袆,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记者容二王之后与?礼之,礼奉茧之世妇。○单音丹。茧,古典反。与音馀,注同。袆音晖。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问者之辞。○率音类,又音律,又所律反。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缫,每淹大总,而手振之,以出绪也。○縿,悉刀反,下同;《说文》作缫,云抽茧出丝也,以此为旒縿字,音所咸反。盆,蒲奔反,淹也。掩,本亦作淹,徐於验反,又於敛反。
[疏]“古者”至“至也”。○正义曰:此一节广明孝子报亲,养蚕为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蚕室”者,谓官家之桑,於处而筑养蚕之室。○“近川而为之”者,取其浴蚕种便也。○“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者,筑宫,谓筑养蚕宫。墙七尺曰仞,言墙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传曰“雉有三尺”,雉字者,误也。棘墙者,谓墙上置棘。外闭,谓扇在户外闭也。○“大昕之朝”,为季春朔日之朝。○“卜三宫之夫人”者,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宫。○“世妇之吉”者,亦诸侯世妇,卜取之吉者。前虽则总举天子、诸侯,此特举诸侯,互言之。○“奉种浴于川”者,言蚕将生之时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风戾以食之”者,戾,乾也。凌早采桑必带露而湿,蚕性恶湿,故乾而食之。○“岁既单矣”者,单,尽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遂献茧于夫人”者,蚕是妇人之事,故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者,所举奉处重。○“遂副、袆而受之”者,既拟于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袆衣,受此所献之茧。○“因少牢以礼之”,接献茧之世妇。○“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者,率,法也。夫人曰:“献茧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义,故问之也。○“及良日,夫人缫”者,良日谓吉日,宜缫之日,明缫更择吉利之日,日至而后,乃夫人自缫。○“三盆手”者,犹三淹也。手者,每淹以手振出其绪,故云“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者,以夫人亲缫,三盆,以手振出其绪讫,遂布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既据诸侯言之,则夫人唯一人。世妇之吉者,此杂互天子而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诸侯唯世妇之吉者养蚕。缫非一人而已,唯云“世妇之吉”者,择其吉者以为主领,非唯一人而已。○“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者,前云解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养蚕,是妇人之事,妇人不与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其实养蚕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注“副袆”至“后与”。○正义曰:案《内司服》注云“唯二王后袆衣”,与此注同。案《明堂位》鲁公夫人亦用袆衣,此不言者,鲁为特赐,非常法。此据常者,故不言。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斯须,犹须臾也。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子,读如不子之子。谅,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易,以豉反,下同。子,如字,徐将吏反,及下注同。谅音亮,下同。油音由。乐乐,并音洛,下“不乐”同。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躬,身也。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众不生慢易焉。极,至也。○争,争斗之争。故德煇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众莫不承顺。理,谓言行也。○煇音辉。行,下孟反,下“理行”、“而行”皆同。故曰:‘致礼乐之道,而天下塞焉,举而错之无难矣。’塞,充满也。○而措,本又作错,七故反。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减,犹倦也。盈,犹溢也。乐以统情,礼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而进之,以能进者为文。溢而使反,以能反者为文。文,谓才美。○减,胡斩反,又古斩反,下同。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报,皆当为褒,声之误。○销音消。报,依注音褒,保毛反,下音同。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疏]“君子”至“一也”。○正义曰:此一节已具於《乐记》,但记者别人,故於此又记之,其义已具在《乐记》故於此不繁文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公明仪问於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为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於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公明仪,曾子弟子。○养,羊尚反,后皆同。与音馀。先,悉荐反。参,徐所材反。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亲,敢不敬乎?遂,犹成也。○莅音利,又音类,本又作涖。陈,直觐反。烖音灾。“於亲”,本又作“烖及於身”。亨、孰、膻、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然,犹如也。○亨,普彭反。荐,将见反。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无朝夕,言常行无辍时也。放,犹至也。准,犹平也。○遗,如字,又于季反。乐音岳,皇五孝反。溥,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放,甫往反,下同,至也。准,诸尹反,平也。辍,张劣反。《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断,丁管反。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劳,犹功也。○匮,其媿反,下同。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思慈爱忘劳,思父母之慈爱已而自忘已之劳苦。○施,始豉反。父母爱之,嘉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无怨,无怨於父母之心。○恶,乌路反。父母有过,谏而不逆。顺而谏之。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喻贫困犹不取恶人物以事亡亲。
[疏]“曾子”至“礼终”。○正义曰:此一节以下至“可谓孝矣”,广明为孝子之事,今各依文解之。○“孝有三”者,大孝尊亲,一也,即是下文云“大孝不匮,圣人为天子者”也。尊亲,严父配天也。○“其次弗辱”,二也,谓贤人为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庙祭祀,不使倾危以辱亲也。即与下文“中孝用劳”亦为一也。○“其下能养”,三也,谓庶人也,与下文云“小孝用力”为一。能养,谓用天分地,以养父母也。○“先意承志,谕父母於道”者,先意,谓父母将欲发意,孝子则预前逆知父母之意而为之,是先意也。“承志”,谓父母已有志,已当承奉而行之。“谕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意前,或在父母意后,皆晓谕父母,将归於正道也。○“五者不遂,烖及於亲,敢不敬乎”者,遂,犹成也。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烖害必及亲,所以为非孝。然则君子於上五者,岂敢不敬而承之者乎?○“亨、熟、膻、芗,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者,言亨、熟、膻、芗之美,先自口尝而后荐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养。○“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原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己”者,言尝荐美食,但是养也,非论孝子。言若人将为孝,曰此子百行皆美,一国之人称扬羡愿。然曰如此,是羡原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所谓孝也已,谓然而令人羡原如此,乃所谓孝也。○“众之本教曰孝”者,言孝为众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则《孝经》云“孝者德之本”,又云“教民亲爱,莫善於孝”,是众行之根本以教於民,故谓之孝也。○“其行曰养”者,言不能备孝之德,其唯行奉上之礼,但谓之养者也。○“养可能也,敬为难”者,言供养父母可能为也,但尊敬父母是为难也。○“敬可能也,安为难”者,其敬虽难,犹可为也,但使父母安乐为难也。○“安可能也,卒为难”者,卒,终也,父母在日,使之安乐,犹可能也;但父母没后,终身行孝,是为难也。○“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者,解卒为难之事。其卒者,谓父母既没之后,谨慎奉行其身,恒在善道,不遗与父母恶名。孝子如此,可谓能卒矣。○“仁者仁此者也”,此,谓孝也。言欲行仁者,先仁恩於此孝也。言欲行仁於外,必须行仁恩於父母也。故云“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履,践履也。言欲行礼於外者,必须履践此孝者也。○“义者宜此者也”,言欲行义於外者,必须得宜於此孝也。行孝得宜,乃可施义於外。○“信者信此者也”,言欲行诚信於外,须诚信於孝道。言行孝道诚信,始可诚信於外。○“强者强此者也”,言欲强盛於外者,必须强盛於孝道。言行孝道强盛,则能强盛於外。○“乐自顺此生”者,自,由也。言身之和乐,由顺从孝道而生。若能顺从孝道,则身和乐。“刑自反此作”者,言身受刑戮,由反此孝道而兴作。若违反孝道,则刑戮及身。○“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但此以下事异,故更言“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者,置,谓措置也,言孝道措置於天地之间,塞满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谓感天地神明也。○“溥之而行乎四海”者,溥,布也。布此孝道而横被於四海,言孝道广远也。“溥”字,而定本作“傅”。傅,溥古字,溥著之名,义俱通,其义如此一也。○“施诸世后世而无朝夕”者,诸,於也,谓施此孝道於后世,而无一朝一夕而不行也。终长行之,言长久。○“推而放诸东海而准”至“北海而准”者,推,谓推排也;放,至也。诸於也。言推排孝道至於四海,能以为法,准平而法象之,无所不从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者,《诗·大雅·文王有声》之诗,美武王也。言武王之德能如此,今孝道亦然,四海之内,悉以准法而行之,与武王同,故引以证之。○“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者至“此之谓礼终”,亦是曾子之言,以语更端,故更云“曾子”。○“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者,以庶人思父母慈爱,忘躬耕之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者,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义,心无劳倦,是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者,匮,乏也,广博于施,则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备物,谓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如此即是大孝不匮也。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善如尔之问也!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曾子闻诸夫子述,曾子所闻於孔子之言。○数,色主反,下同。瘳,丑留反,差也。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顷当为跬,声之误也。予,我也。○顷,读为跬,缺婢反,又丘弭反。一举足为跬,再举足为步。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径,步邪趋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无忿怒,忿怒之言,当由其直,直则人罚墬不敢以忿言来也。○径,古定反。邪,似嗟反。趋,七俱反。
[疏]“乐正”至“孝矣”。○正义曰:此一节论乐正子春伤其足而忧,因明父母遗体不可损伤之事。○“无人为大”者,言天地生养万物之中,无如人最为大。故《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也。○“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者,非直体全,又须善名得全。若能不亏损,形体得全,不损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者,顷,跬也,谓一举足。君子於一举足之间,不敢忘父母也。言忘之恐有伤损。○“是故道而不径”者,谓於正道而行,不游邪径。正道平易,於身无损伤。邪径险阻,或於身有患。○“舟而不游”者,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则安,浮水则危。○“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者,以其不忘父母之遗体,故不敢以先父母遗馀之体而行历危患处。○“恶言不出於口”者,悖逆恶戾之言不出於口,为人所贱也。○“忿言不反於身”者,谓己之言必能正直,人则服之,故他人瞋忿之言不反於身。定本反於身,作“及”字。○“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者,总结举足、出言二事,身及亲并不羞辱,可谓孝矣也。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贵,谓燕赐有加於诸臣也。尚,谓有事尊之於其党也。臣能世禄曰富。舜时多仁圣有德,后德则在小官。
[疏]“昔者”至“尚齿”。○正义曰:此前经明孝,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故下云“孝弟发诸朝廷”,事兼孝弟也。各随文解之。今此一经,论四代悌顺尚齿之义。○“有虞氏贵德而尚齿”者,虞氏帝德弘大,故贵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者,夏后之世渐浇薄,不能贵德而尚功,功高则爵高。既贵其官爵,德虽下而爵高者则贵之,由道劣故也。故贵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者,殷人又劣於夏,但身有功,则与之重爵。殷家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贵之,故云贵富。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者,周人又劣於殷,敬爱弥狭。殷人疏而富者,犹贵之,周人於已有亲乃贵之。就此之中,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齿。○注“贵谓”至“小官”。○正义曰:郑恐经云贵者,皆班序在上,故名之“贵,谓燕赐有加於诸臣”。凡四代朝位班序,皆以官爵为次,悉皆重爵,而夏后氏贵者,但於爵高者加恩赐。云“尚,谓有事尊之於其党也”者,谓德、爵、富、亲各於其党类之中而被尊也。云“舜时多仁圣有德,后德则在小官”者,郑解虞氏贵德之意,以舜时仁圣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来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后来者则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故有虞氏贵之,所以燕赐加於大官,俗本“后德”多作“小得”字。
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言其先老也。
[疏]“虞夏”至“事亲也”。○正义曰:此一经覆述虞、夏以来尚年之事。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言虞、夏、殷、周虽是明盛之王也,未有遗弃其年者,悉皆尚齿,更无他善以加之。○“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者,从虞、夏以来,贵年是久矣。○“次乎事亲也”者,言贵年之次弟,近於事亲之孝,除孝则次弟也。
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於朝,君问则席;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同爵尚齿,老者在上也。君问则席,为之布席於堂上,而与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鲁哀公问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毕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许,异其礼而已。○於朝,直遥反,后皆同。弟音悌,下及下注同。为,于伪反。
[疏]“是故”至“廷矣”。○正义曰:此一经明朝廷之中行於弟也。○“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者,此因前文尚年,以是之故,朝廷之中同爵则尚齿,官爵同者则贵尚於齿,四代皆然。○“七十杖於朝,君问则席”者,以其尚齿,故七十者许之据杖於朝。若君有问,则布席令坐也。○“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者,年已八十,不但杖於朝而已,见君揖则退,不待朝事毕也。若君有事问之,则就其室,是逊弟敬老之道通达於朝廷矣。○注“凡朝”至“而已”。○正义曰:知“朝位立於庭”者,案《燕礼》大射,君与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于阼阶上。是也。云“鲁哀公问於孔子,命席”者,《儒行》文。云“不俟朝,君揖之即退”者,案《燕礼》:大射,卿、大夫立于庭,北面。君降自阼阶,南乡,尔卿。卿西面,尔大夫。大夫皆少进,皆北面。尔,谓揖也。於时老臣,君揖则退,不待朝事毕也。则於路寝门外,曰视朝,亦揖竟即退,不待朝事毕也。云“老而致仕,君或不许,异其礼而已”者,案《曲礼》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是或不许也。此经中所云,是君不许者,故“七十杖於朝,君问则席”,又“八十不俟朝”,是异其礼。若其致事,君许,则《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君许者与此异。
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达乎道路矣。锴,雁行也。父党随行,兄党雁行。车、徒辟,乘车、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发杂色也。任,所担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并,步顷反,徐扶顶反。辟音避,注同。行,户刚反,下同。担,都甘反。少,诗照反,下同。居乡以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弟达乎州巷矣。老穷不遗,以乡人尊而长之。虽贫且无子孙,无弃忘也。一乡者五州。巷,犹闾也。○遗如字,一本作匮,其媿反。长,丁丈反,下文皆同。
[疏]“行肩”至“巷矣”。○正义曰:此一节明弟通达於道路。○“行,肩而不并”者,谓老少并行,言肩臂不得并行,少者差退在后,则朋友肩随是也。○“不错则随”者,若兄党为雁行之差错,是父党则随从而为行。○“见老者则车、徒辟”者,谓少者或乘车,或徒步,若逢见老者则辟之。○“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者,任,谓担持,言班白不以所任之物行于道路。少者必代之,是弟通达於道路。○注“错雁”至“雁行”。○正义曰:错,参差,假雁行为行。“父党随行”,《王制》文。
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而弟达乎獀狩矣。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为军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从力役之事也。颁之言分也。隆,犹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谓竭作未五十者。春猎为獀,冬猎为狩。○甸,田见反。颁音班。獀,本亦作廋,音蒐,所求反。狩音兽。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弟达乎军旅矣。什伍,士卒部曲也。《少仪》曰:“军尚左,卒尚右。”○卒,子忽反,下同。
[疏]“古之”至“旅矣”。○正义曰:此一节明弟道达於獀狩。○“古之道”者,谓作记之人在於周末,於时力役烦重,却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五十不为甸徒”者,谓方八里之甸。徒谓步卒。军法:八里出长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谓之甸者,以供军赋及田役之事。五十者气力始衰,不为此甸役徒卒。○“颁禽隆诸长”者,谓四十九以下,田毕颁禽之时,多长者。○注“四井”至“为狩”。○正义曰:“四井为邑”至“六十四井也”,《司马法》文。云“以为军田出役之法”者,谓一甸之中,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君田役事,故云“以为军田出役之法”。云“五十始衰,不从力政之事也”者,《王制》文。云“谓竭作未五十”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若田与追胥竭作之时,此未五十者犹任田役,故颁禽之时,多此长者。云“春猎为獀,冬猎为狩”,《尔雅·释天》文。经云“獀、狩”,夏苗、秋狝可知也。○注“什伍”至“部也”。○正义曰: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士谓甲,士卒谓步卒。在军旅之中时,主帅部领团曲而聚,故云部曲。
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死之,死此孝弟之礼。○放,方往反。
[疏]“孝弟”至“犯也”。○正义曰:此一节总论结上文。○“孝弟发诸朝廷”者,即上文“而弟达乎朝廷”是也。在上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则孝之次也。此经总结前诸文,故云“孝弟”也。○“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者,言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獀狩、军旅,无处不行孝弟以教众庶也。故众以道理之义死於孝弟也。言行孝弟,虽死不舍,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於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学,周小学也。先贤,有道德,王所使教国子者。○食音嗣,下同。更,古衡反,下同。大学音泰,下“大学”、注“大下”皆同。
[疏]“祀乎”至“教也”。○正义曰:此一节广明孝弟之道,养三老五更及齿学之事。○“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者,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故《乐记》云“祀文王於明堂”是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者,案《孝经》云“虽天子必有父”也,注“谓养老也”。父,谓君老也。此食三老而属弟者,以上文祀文王於明堂为孝,故以食三老五更为弟,文有所对也。○“祀先贤於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者,以先贤有德,故祀之,令诸侯尊敬有德,故云“教诸侯之德”。此西学,郑注云“周小学”,则周之小学在西郊,则《王制》云“养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是也。○注“祀乎”至“子者”。○正义曰:云“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者,郑以《乐记》武王伐纣,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彼谓文王庙制如明堂,武王伐纣后而祀之。恐此“祀乎明堂”亦与彼同,故云谓“宗祀文王”也,实於明堂之中。知者,以此经广明周法,故五者天下之大教,明不独论武王,是指周公制礼之后、宗祀文王也。云“西学,周之小学也”者,谓虞庠也。以祀先贤,明於虞庠小学,故《大司乐》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书》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贤所通之经,各於所习之学。若瞽宗则在国,虞庠为小学者,则在西郊。今祀先贤,则於西郊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割牲,制俎实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以乐侑食也。教诸侯之弟,次事亲。○酳音胤,又事觐反。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齿於学之谓也。”
[疏]“食三”至“子齿”。○正义曰:此一节明养三老五更之礼而竭其力,下象其德。○“天子袒而割牲”者,谓牲入之时,天子亲割也。○“执酱而馈”者,谓食之时,亲执酱而馈也。○“执爵而酳”者,谓食罢,亲执爵而酳之也。○“冕而总干”者,干,盾也。亲在舞位,持盾而舞也。○“是故乡里有齿”者,以天子敬老,乡里化之,故有齿也。○“老穷不遗”者,老而被养,故在下年老及困穷者,皆化上而养之,故不见遗弃。作记者以老弱被尊养,人皆化上,故“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所致此养三老五更於大学,故此化而来。○“天子设四学”者,谓设四代之学。周学也,殷学也,夏学也,虞学也。○“当入学而大子齿”,天子设四学,以有虞庠为小学,设置於四郊,是天子设四学,据周言之。“当入学而大子齿”者,当入学之时,而大子齿於国人,故云“而大子齿”。○注“四学”至“庠也”。○正义曰:皇氏云:“四郊虞庠,以为四郊皆有虞庠。”
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问其国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见之。○守,手又反,本亦作狩。竟,居领反。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西行,东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过者,谓道经之则见之。
[疏]“天子”至“可也”。○正义曰:此一节亦明尚齿贵老之义。○“天子巡守”者,谓巡行守土诸侯。○“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谓天子问此诸侯之国内有百年之人,天子则先往就见百年者。○“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者,既未满百岁,不可一一就见。若天子、诸侯因其行次,或东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闾里之旁,不敢过越而去,必往就见之。○“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者,谓八十九十之人,虽不当道路左右,欲共言论政教,君即往就之可也。
壹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族,三命不齿。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谓乡射饮酒时也。齿者,谓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国之卿也,不复齿,席之於宾东。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谓既一人举觯乃入也,虽非族亦然,承“齿乎族”,故言族尔。○复,扶又反,下文注“将复入”同。觯,之豉反。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谓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与之为礼,而后揖卿、大夫、士。
[疏]“一命”至“爵者”。○正义曰:此一节明乡里之中敬齿之法。○“一命齿于乡里”者,此谓乡射饮酒之时,身有一命官者,或立或坐,齿与乡人同。○“再命齿于族”者,谓身有再命之官,其命既高,乡人疏者,虽复年高,不与之齿。但族亲之内,计长幼为班序。○“三命不齿”者,谓身在三命官,其命转尊,不复齿於亲族,谓特坐宾东。○“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者,若此饮酒之时,族亲之内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乃始后入,故云“不敢先”也。○注“此谓”至“族尔”。○正义曰:此经云齿于乡里,齿于族,未知何时如此,故明之云“谓乡射饮酒时”,乡射,谓乡人询众庶而为射,於时先行饮酒之礼,是乡射有饮酒者也。又云饮酒者,谓乡人饮酒及党正饮酒。此注乡射饮酒,兼此三义也。今案《仪礼·乡饮酒》及《乡射》无“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族”之文。此一命、再命之文,在《党正》。故郑注《乡饮酒》云“此篇无正齿位之事”是也。虽无正齿位之事,其实《乡射》、《乡饮酒》亦有正齿位之礼,但文不备也。故此云乡射饮酒,以总正齿位之事也。云“齿”者,谓以年次立若坐也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知者,《乡射》云“大夫受献讫,及众宾皆升就席”。於时虽立,至彻俎即坐。《乡射记》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见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国之卿也”者,据诸侯言之,谓当饮酒之时,若天子国党正饮酒,三命不齿,谓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此经虽据诸侯,亦谓党正饮酒,故云“三命不齿”。郑注:“三命,列国之卿。”若其乡饮酒,诸侯之国,但爵位为卿大夫,虽再命一命,皆得不齿,以乡饮酒宾贤能,其宾必少,其得爵为卿大夫者,必年长於宾,故在宾东,西面,而不齿。若《党正》饮酒“以正齿位”,其宾必长,故天子、诸侯之国,三命乃不齿。知乡饮酒爵为卿大夫乃不齿者,案《乡饮酒》云:“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注云:“席此二者於宾东,尊之,不与乡人齿也。”天子之国,三命者乃不齿。於诸侯之国,爵为大夫则不齿。是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者,谓诸侯之国。若天子党正饮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齿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宾东。云“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谓既一人举觯乃入也”者,族七十者初饮酒之时,则与众宾先入,此三命者,得为待献宾献介献众宾之后,至一人举觯之时,乃始入也。故《乡饮酒》、《乡射记》皆大夫乐作之前、一人举觯之后,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礼自当一人举觯之时,纵令无族人七十者亦当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乡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记人之意,以身有三命,应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齿上老,故云“不敢先”尔,是以郑注云“虽非族亦然”,但乡人长老皆上之,既入,然后始入。此有“族有七十”者,熊氏云“谓党正饮酒,故‘正齿位\\’,故有七十。若《乡饮酒》之礼,则无七十者。故《乡饮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天子有善,让德於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於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荐,进也。成诸宗庙,於宗庙命之。《祭统》有十伦,六曰见爵赏之施焉。○见,贤遍反。施,始豉反。
[疏]“天子”至“顺也”。○正义曰:此一节明有善让於尊上,示以敬顺之道,不敢专也。
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教不伐以尊贤也。立以为《易》,谓作《易》。易抱龟,易,官名,《周礼》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梦之占。○卷,古本反。知音智。断,丁乱反。
[疏]“昔者”至“贤也”。○正义曰:此一节亦明其不敢专辄尊贤之事也。○“立以为《易》”者,圣人谓伏羲、文王之属,兴建阴阳天地之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阴阳,以作《易》,即今时易也。“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为占《易》之官,抱龟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亲执卑道,服衮冕北面。○“必进断其志焉”者,言天子虽有显明哲知之心,必进於龟之前,令龟断决其已之所有为之志,示不敢自专,以尊敬上天也。○“教不伐以尊贤也”者,有善称人,有过称己,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贤人也。○注“周礼”至“之占”。○正义曰:此称官者,於《周礼》称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郑注云:“言兆形似玉、瓦、原之亹罅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颛顼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三《易》者,《连山》、《归藏》、《周易》,杜子春云:“《连山》,宓戏。《归藏》,黄帝。”郑作《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三梦: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
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报物,以脩宫室,以治百事。谓齐之前后也。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如惧不及见其所爱者。○恐,曲勇反。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奠之,谓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属。如语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语亲而未见答。○以语,鱼预反。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将弗见然。宿者皆出,谓宾助祭者事毕出去也。如将弗见然,祭事毕,而不知亲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见出也。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然。思念既深,如睹亲将复入也。陶陶遂遂,相随行之貌。○陶音遥。遂,本又作燧,音遂。是故悫善不违身,耳目不违心,思虑不违亲。结诸心,形诸色,而术省之,孝子之志也。术当为述,声之误也。○思,息嗣反。术,义作述。
[疏]“孝子”至“志也”。○正义曰:此一节明孝子将祭祀之时,颜色容貌务在齐庄卑诎,思念其亲存也。○“以虑事”者,言孝子先齐庄其心,以谋虑祭事。○“以具服物”者,以备具衣服及祭物。○“以治百事”者,谓齐前后,凡治百众之事。○“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者,言孝子色必温和,行必战恐,其形貌如似畏惧不及见亲之所爱然。止由如是,言心貌必温。○“身必诎”者,言孝子设奠及酳之时,容貌温和,身形必卑诎。○“如语焉而未之然”者,如以语谘白於亲,而未之见报答者。○“宿者皆出”者,谓助祭所宿之宾,今祭事已毕,并皆出去。孝子其立,卑柔静默,然后以正定心意,以思念其亲,如似将不复见颜色出然。○“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然”者,孝子思念亲深,及至祭后想像亲来形貌,陶陶遂遂,如似亲将复反。更入然。○“是故悫善不违身”者,以孝子思念亲深,为是之故精悫纯善之,故行不违离於身,言恒悫善也。○“耳目不违心者,言忠心思虑不违於亲,无时歇也。○“结诸心”者,言思念深结积於心。○“形诸色”,思念其亲,形见於色。○“而术省之”者,术,述;省,视也。言思念其亲,但遍循述而省视之,反覆不忘也。此乃孝子思念亲之志也。
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周尚左也。
[疏]“建国”至“宗庙”。○正义曰:此一节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庙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郜大鼎,纳於大庙。”何休云:“质家右宗庙,尚亲亲,文家右社稷,上尊尊。”此说与郑合,故郑云“周尚左”也。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翻译:孔子说:学习并时常温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从心里感到高兴吗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知止(4)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孔子说:学习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温习它,不是件高兴的事吗?有好朋友从远方来(互相切磋,增长学问),不是件快乐的事吗?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怨恨别人,不也是有道德的表现吗? 2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原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翻译】孔子说:“学习了知识又时常实践,不也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是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知道)我,我却不怨恨(生气)

夫总群圣之道者,莫大乎六经。绍六经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战国初兴,至化陵迟,异端并作,仪、衍肆其诡辩,杨、墨饰其淫辞。遂致王公纳其谋,以纷乱於上;学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犹洚水怀山,时尽昏垫,繁芜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

《礼记正义》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文献。汉代有郑玄作注,唐代有孔颖达为之正义,都是古人对《礼记》的注释,是今人阅读研究《礼记》的重要版本。今归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由吕友仁先生拟影印宋绍熙刻本《礼记正义》校以

论语注疏,又称论语正义,又称论语注疏解经,魏何晏注,宋邢昺疏,二十卷。案何注皇疏皆以道家思想解论语,又於名物制度无所考订,颇为学人所不满。北宋时遂由朝廷於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昺删除皇疏之文,而归向儒学本来之义理,又加名物制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春秋左氏》,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左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

谦受益,满招损,谦虚纳百福。成功的人物没有不谦虚的,不谦虚就会很快失败。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而拜,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谦虚得到天道、地道、人道的呵护,就连鬼神都呵护它。“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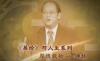
坤卦是八卦中至柔至顺的一卦。由六个阴爻组成,底部三个阴爻为下坤卦,上面三个阴爻为上坤卦。由下到上依次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坤卦的卦辞:元、亨、利牝(bi母)马贞。用母代表坤卦,用马代表健行,有恒心。每一个人都有阴性的魂和阳性的魂。

第四讲:自强不息——乾卦,乾卦是天下第一卦,代表生命的开始。乾卦由由下到上六条横线组成,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一到九的奇数代表阳,偶数代表阴,九最大代表无穷的力量,六居中代表安静。在古代,龙是三栖动物。

第三讲:八卦的卦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之间相互转化。“女子虽弱,为母则强”。八个卦象的写法: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巽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第二讲:《易经》的由来,易经的发展三位圣人:伏羲氏、周文王和孔子做了巨大的贡献。开天辟地之后,人要怎样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和发展,让伏羲氏产生了忧患意识,易经起源于忧患。易经的核心是居安思危。伏羲氏抬头观天象,观察天体的运转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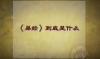
第一讲:《易经》是什么?易经是“不学不会,学了不一定会,会来终身受用”。易经的重点是修德行善。易经包括义理和象数。义理指为人处事的道理;象数指卦象的计算规律。易经是“观天道立人道”,真正的儒家是由内而发,西方有哲学派别认为“人是唯一使用符号的动物”。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谷梁传》所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lè)乎?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学而》) 2 曾子曰:吾(wú)日三省(xǐng)吾(wú)身,

一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

[问]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生异类,本为养人。禁之宰杀,逆天甚矣。[答]既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奈何不知万物为天地之赤子。赤子之中,强凌弱,贵欺贱,父母亦大不乐矣。倘因食其肉,遂谓天所以养我,则虎、豹、蚊、虻,亦食人类血肉,将天之生人

不管《三字经》作者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在有限篇幅当中赞扬了两位非常有才学的女子,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蔡文姬,而另一位是我们比较陌生的谢道韫。谢道韫是东晋时期著名才女,我们知道有一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之家和寻常百姓之家是对着

大家都知道,人最好是从岁数很小时,就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就开始勤奋地学习,就开始接受良师的指导。但人世间的很多事是难以预料的。很多人或说更多的人,因种种原因错过了最佳的读书和受教育年龄。那年岁大的人还应不应学习?年岁大的人学习了还能不能够取

学习离不开刻苦的精神,《三字经》对这点当然不会放过,它也非常强调,所以《三字经》用两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稍微有点那么极端的故事,来张扬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我们后来把这两个故事并成一个成语叫悬梁刺

三字经一直是通过讲故事,把一些深刻的道理,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既然是讲学习,谁最合适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谁是一个学习的楷模呢?毫无疑问是孔子。所以接下来三字经讲:昔仲尼,师项橐(驼)。古圣贤,尚勤学。字面意思非常清楚,想当年孔老夫子拜项橐为师

接下来,《三字经》又用12个字讲述了明朝的败亡。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也就是说永乐帝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到了崇祯就在煤山去世,这位皇帝在人世间活了只不过33岁,他是1611年出生,1644年在煤山上吊自杀,不少人认为,崇祯实在并不是一个坏皇

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明太祖,久亲师的故事,也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长时间的亲自率领军队进行征战,最后成功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明朝,那么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他是用哪些手段、方法、理念,换句话说,他是怎样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是高度集

根据我所采用的这个版本,元朝以后的明朝是《三字经》讲述的最后一个朝代。一般认为讲述到后来的清朝乃至民国都是后来比较近的人离今天比较近的人增补的所以我们讲《三字经》,在历史部分就讲到明朝。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这样四句12个字是讲述了明太

在中国历史上接着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的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那就是元朝,三字经讲元朝时是这么讲的:至元兴,金绪歇。有宋世,一同灭。并中国,兼戎翟。什么意思呢?到了元朝兴起时金朝也灭亡了,因为金朝是被元朝和南宋联合灭亡的。有宋氏 一同灭,连宋朝捎带着也灭亡了

赵匡胤即位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抗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皇帝的位子还没坐暖呢就御驾亲征,费了不小的劲才把这两个手握重兵的节度使镇压下去,这件事使赵匡胤心里怎么都不踏实,所以有一天他就单独召见赵普这位自己主要的谋士,跟他商量。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