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
内容提要敦煌本《坛经》被发现后,引起学术界、佛教界持久的兴趣,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共发表有关它的录校本近三十种。但是,诸录校本都还不能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就是一个新的努力。《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将《坛经》分成若干章进行整理。整理由正文、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注释、分段标点复议、疏义、原始资料等六部分组成。一、“正文”乃此次录校勘正的《坛经》正文,并重新分段、标点。二、“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包括校记与复议。三、“注释”部分对《坛经》经文中的若干词语进行注释。四、“分段标点复议”部分主要对诸家录校本的分段、标点中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五、“疏义”部分对《坛经》经文进行疏义。六、“原始资料”相当于附录,照录诸种敦煌本《坛经》的原文,可与诸敦煌本《坛经》的照片相参看。本文是《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的首章,读者从中可以窥豹一斑。
关键词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
敦煌本《坛经》被发现后,引起学术界、佛教界持久的兴趣,诸种录校本不断涌现。据我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共发表录校本近三十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诸录校本都还不能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就是一个新的努力。
《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将《坛经》分成若干章进行整理。整理由正文、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注释、分段标点复议、疏义、原始资料等六部分组成。说明如下:
一、“正文”乃此次录校勘正的《坛经》正文,并重新分段、标点。
为方便起见,本文对《坛经》正文之每章、每节、每句均予以编号(以下称为“章节号”)。章节号以“§”领起,依次分为三段:章序号、节序号与句序号,用小数点隔开。章节号放在“[]”中,标注在每句经文之后。
二、“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包括校记与复议)
校记为笔者此次录校时所作。录校时以敦博本为底本,以斯本、旅博本、北本、北残片、西夏本为校本。因旅博本、北本、北残片、西夏本均为残本,故仅参校现有文字,并在起讫时出注说明。叙列校记时,首先以章节号领起《坛经》正文,然后逐句出校记。如某句无出校文字,亦罗列该句,然后下注“无”。校记的写法,参见《藏外佛教文献》第八辑所载《录文校勘体例》。
复议为对国内六家有代表性的敦煌本《坛经》录校本录校的考察。之所以选择此六家,是因为近年来敦煌本《坛经》的研究热潮已经由国外转入国内,主要新成果均在国内,而上述六家代表了十余年来我国在敦煌本《坛经》录校方面的最高水平。复议意见随文记入校记。所用六家录校本,按照其出版的先后出版次序,罗列如下:
郭本,指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月。郭本当时没有条件参校敦博本、旅博本。故涉敦博本、旅博本时对郭本不予复议。又,郭朋尚有《〈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年6月)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等两种《坛经》整理本问世。但因巴蜀书社本《坛经导读》为郭朋先生的最新成果,故本书之复议,一般均依《坛经导读》为准。特别是遇到三本意见不一致时,完全依据后出之《坛经导读》,而一般对前两种整理本的不同意见不予说明。但遇到前两种整理本涉及,而《坛经导读》没有涉及,且复议又必须予以讨论的问题时,则适当采用前两种整理本的观点,此时随文注明出处。
周本,指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12月。
邓荣本,指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此外,邓文宽先生另有《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湾如闻出版社,1997年2月。以下简称“邓本”)问世。同样,为了尊重两位先生的最新成果,本书复议时一般以后出版的邓荣本为准。但遇到邓荣本未予涉及而邓本予以论述的问题,以及邓本优于邓荣本的问题,则对邓本予以复议。
李本,指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本文仅对其录校部分进行复议,故称“李本”。
杨本,指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5月。杨曾文此书为修订本,初版时书名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本书复议亦从上例,以新版为依据。
潘本,指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2001年6月。潘重规此书初版于1995年7月,名《敦煌坛经新书》,亦由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发行。其后增补“附册”,更名为《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再版发行。复议以再版本为依据。
应该说明的是,学术有先后继承,后来者应该超越前人,也超越先前的自我。在此将上述六种录校本按照出版时间依次排列并复议,就是为了尊重学术发展的历史。对待学者个人,如果成果有先后之别,自然也应该采用后发表者,以示尊重。如杨本1993年初版,2001年修订再版,在此主要依据再版本。但我发现潘本2001年的新版本与1995年的老版本完全一样,未作修订。但也未作诸如“本书应该修订,但因故未能进行”之类的声明。这或者是因为作者观点未变,无须修订的缘故吧。本文斟酌再三,决定按照既定体例,对潘本,亦以2001年新本为据,并按照出版时序,排列在六本之最后。
三、“注释”部分对《坛经》经文中的若干词语进行注释。
四、“分段标点复议”部分主要对诸家录校本的分段、标点中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至于可分可不分、可断可不断、或可句可逗之处,均不予讨论。
五、“疏义”部分对《坛经》经文进行疏义。
六、“原始资料”相当于附录,照录诸种敦煌本《坛经》的原文。可与诸敦煌本《坛经》的照片相参看。
录文中,每行行首的数字为该行的行号。行末的“//”号表示该行文字结束;“/ ”号表示该行文字尚未结束,但本章文字已经结束。下一章将接续录文。
所用诸本如下:
敦博本,指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77号,从照片看,应为缝缋装,首尾完整。
斯本,指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5475号,从照片看,应为缝缋装,首尾完整。
旅博本,指原藏于旅顺博物馆敦煌本《坛经》,从照片看,亦应为缝缋装。现下落不明,仅存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三个半叶照片。其首部半叶照片为《坛经》,尾部两个半叶照片为其他文献。
北本,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敦04548背.1号(旧编:岗48号,缩微胶卷号:8024),卷轴装,首残尾存。
北残片,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敦08958号,卷轴装,残片,仅5行。
西夏本,指西夏文《坛经》残片。二十世纪20年代以来续有发现,现共12个残片。综合研究有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参用此文。
§00 标题
一、正文[§00.01.~§00.05.]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00.01.]
--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00.02.]一卷[§00.03.]兼授
无相戒[§00.04.]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00.05.]
二、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
§00.01.南(1)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2)若波罗蜜经
(1)“南”,底本、斯本、旅博本自此起。
(2)“般”,底本作“波”,据斯本、旅博本改。
周本、邓本、杨本、潘本校改作“般”。邓荣本以“般”为正而未改。李本径改作“般”而未出校记。
“波”、“般”因字音相同而误,应校改。
§00.02. 六祖惠能(1)大师於(2)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1)“惠能”,底本、斯本、旅博本同。
郭本出校称“惠”通“慧”,录文中作“惠能”,但自己行文时作“慧能”;周本、杨本校改为“慧能”;邓荣本认为“惠”、“慧”互通,虽出校但录为“惠能”;邓本校改为“惠能”;李本、潘本照录为“惠能”,不出校。
笔者以为,诸敦煌本通篇均作“惠能”;且早期诸著作,大抵均称“惠能”。后因“慧”、“惠”可通,方才逐渐改成“慧能”。故敦煌本录校本应保留“惠能”原名,不作校改。
杨本校记谓:“题目及正文中的‘慧能’皆写作‘惠能’;‘智慧’写作‘智惠’等。今一律改为‘慧能’、‘智慧’、‘定慧’。”故以下凡遇杨本改“惠”为“慧”者,如非特殊情况,一般不出注。
(2)“於”,郭本、李本因是简体字本,故改作“于”。以后凡由于简繁体原因,造成郭本、李本文字与敦煌本有异者,均不出注。
§00.03.一卷
无。
§00.04.兼授(1)无相戒
(1)“授”,底本、斯本、旅博本均作“受”,理校作“授”。
郭本、李本、杨本照录作“受”;邓荣本谓“受”同“授”,但未校改原文;邓本、潘本校改为“授”;周本的意见参见本句校记〔2〕。
笔者认为,虽然敦煌本《坛经》的抄写者“授”、“受”不分,但“授”、“受”两者字义有别。如为“授”,则表示惠能向参与法会的全体信徒传授无相戒;如为“受”,则表示作者法海是一个曾从惠能接受无相戒的僧人。前者是普授,后者是特受。且这里直接涉及对《坛经》性质的认识,涉及到标题的写法,不可不辨。细案《坛经》原文,此处应为惠能向与会信徒普授无相戒,故理校为“授”。
(2)“无相戒”,底本、斯本、旅博本同。
郭本、邓荣本、李本、杨本、潘本均录作“无相戒”,对留空失校。
周本主张“受无相戒”中“相”与“戒”之间的留空表示省去重复之字。并将“受无相戒”补校作“授无相戒受无相戒”。
笔者认为,诸录校本无视留空,失校有误。周本用省略重复字来解释这里的留空,无法成立。详见本章“分段标点复议”的有关部分。
§00.05.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无。
三、注释
南宗--指禅宗惠能系。惠能系起先主要流传于南方。唐开元二十年(732),惠能弟子神会在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上,极力批评流传于北方的禅宗神秀系“师承是旁,法门是渐”,为惠能系争正统。禅宗内部从此产生宗派之诤,出现“南宗”这一名称。后人追溯当时禅宗北宗、南宗分流的情况,亦有“南能北秀”的说法。南宗至后世极盛,被视为禅宗正统。
顿教--神会称惠能系禅法的基本特征为“顿悟”,指斥神秀系北宗主张“渐悟”。“顿教”,即“顿悟之教”。敦煌本《坛经》之所以在标题上揭示“顿教”字样,是为了高扬本宗的理论标志。
最上大乘--“大乘”是印度佛教的主要派别之一,与小乘相对,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应以六度普度众生,以求佛道。中国佛教主要流传大乘,故往往推崇大乘,贬斥小乘。大乘内部又有诸多派别与思想。“最上”为禅宗南宗僧人对本宗的美称,意为禅宗南宗是最高级、最上等的大乘。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为梵文“m⑥ha”的音译,意谓“大”,是美称。“般若波罗蜜”,为梵文“prj㈦⑥-p⑥ramit⑥”音译,意谓“智度”,为大乘佛教六度之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原为印度佛教宣说般若思想的重要经典,汉文有鸠摩罗什译本。印度佛教般若思想主张由智慧而达佛道,亦即所谓“般若是诸佛之母”,在中国影响甚大。但此处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并非指称鸠摩罗什译本,而是借用“般若是诸佛之母”的含义,宣扬惠能的这部《坛经》就是一部可以由般若之智而抵达佛道的经典。
郭本认为:般若思想属于空宗,惠能思想属于有宗。“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插进《坛经》的标题里,实在是不伦不类的。……《般若》之与《坛经》,是空、有异趣、迥不相同的”【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8页。】。其实,惠能佛性论的根基仍是般若思想,惠能听《金刚经》而有悟,一生深受《金刚经》影响就是明证。且如前所述,此处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主要意义是指“以般若智慧成佛之经”,并非指论述般若思想的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其他般若系的某一部经典。郭本认为标题中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指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从而做出上述指责。该观点尚可斟酌。
六祖--此处指惠能。禅宗南宗主张惠能是继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递传的东土禅宗第六代正统祖师。禅宗的不同派别对何人为六祖说法不一。
惠能--唐代僧人,本经的说法者,我国禅宗南宗的创始人,禅宗第六祖。也有人主张他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俗姓卢,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死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唐宪宗(806~820)时谥号“大鉴禅师”。惠能的遗体由其弟子方辩裹紵涂漆,保存至今。现存于广东曲江县南华寺(即古代的宝林寺)。
大师--对佛教僧人的尊称。
韶州--唐代州名,时治所在今广东韶州。
郭朋《坛经校释》称:“韶州,今广东曲江县。大梵寺,在韶州城内。”【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2页。】邓本亦称:“韶州,唐代州名,治所在今广东省曲江县。”“大梵寺,唐时位于韶州城内。”【邓文宽:《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湾如闻出版社,1997年,1页、2页。】类似的说法又可见李申《六祖坛经》【参李申:《六祖坛经》,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31页。】等。
按照上述说法,唐代的大梵寺在唐代的韶州城内,而唐代的韶州城相当于现今的广东省曲江县(马坝),也就是说,大梵寺应该在现今的曲江县(马坝)。但实际上大梵寺在今韶州(韶关)城内。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请教了南华寺的云峰法师。根据云峰法师见告,曲江县治,原在韶关,后迁马坝。故在曲江县治迁移马坝以前,说“韶州,今广东曲江县。大梵寺,在韶州城内”是对的;而在曲江县治迁移马坝以后的今天,再那样说就是错误的。
大梵寺--在今广东韶州城内。因惠能的谥号为“大鉴禅师”,故该寺现名“大鉴寺”。
丁福保《佛教大辞典》引《广东通志》卷二二九谓:“韶州府曲江县报恩光孝寺,在河西。唐开元二年,僧宗锡建,名开元寺,又更名大梵寺,刺史韦宙请六祖说《坛经》处。宋崇宁三年,诏诸州建崇宁寺,致和中改天宁寺。绍兴三年,专奉徽宗香火,赐额曰报恩光孝寺。”据此,该寺乃唐开元二年(714)由僧宗锡所建,初名开元寺,其后改称大梵寺。何时改称大梵寺,详情不清。这一说法为郭本等录校本所从。
但笔者颇为怀疑这一说法的可靠性。首先,惠能早在先天二年(713)已经逝世,但按照上述说法,惠能在大梵寺说法的时间应该在开元二年(714)以后,两者相互矛盾。其次,唐开元初年,诸州均据朝廷敕令修建官寺开元寺。但既是依照敕令修建的官寺,就不应该由僧人个人出面建造。由于唐代敕建之官寺,往往有以现成寺院换额改称者。所以我认为,如果该寺确由宗锡修建的话,则很可能是先由宗锡修建大梵寺,开元二年(714),当地官员将大梵寺换额,改称开元寺。据前述《广东通志》记载,该寺直到宋代还保持着官寺身份,由此反映该寺在当地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这或许是该寺保留至今,且当地耆老至今能明其由来的原因。
施法--佛教认为僧人说法乃是向听法者布施佛法,故称。
坛--原为土筑的台子,用以进行某些仪式或宗教活动。后用来对译梵文“曼荼罗”,指修持佛法时所造的供养佛像、菩萨像、供养具等的台子,其构筑有一定的规范与仪轨。此处指为尊重惠能教法,供他说法用的台子。
经--梵文“sūtra”的意译。佛教传统,凡佛金口所说,方可称之为“经”。非佛所说而妄称“经”者,概为伪经。《坛经》所以被称为“经”,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惠能已经是一个活佛。《坛经》记载当时信徒的称赞:“岭南有福,生佛在此。”“生佛”指惠能。
兼授--《坛经》的主体纪录了惠能在大梵寺主持的某次法会。这次法会的主要内容,如正文§01.01.01.所述,是“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亦即包括“说法”、“授戒”两项。所以,《坛经》标题上的“兼授”,表示本文献所纪录的,除了惠能所说之法外,还兼有惠能为听法者所授的无相戒。当一个文献中兼有其他内容时,敦煌遗书往往用细字于标题、卷次下注出。
无相戒--惠能创立的禅宗戒法。
惠能认为诸法性空,佛性本净。无相戒即以该清净佛性作为戒体。由于佛性无相,实相为空;诸法既空,罪性亦空。所以持戒者心无系缚,远离执著,等视诸戒,犹如虚空。站在上述立场上,惠能对佛教戒律的基本态度即如《坛经》所谓“心平何须持戒”。因此在实际持戒中,并不像其他戒法那样需要有日常的仪轨与行相,故曰“无相戒”。根据《坛经》,授无相戒包括归依自性三身佛、发四弘愿誓、无相忏悔、三性三归依戒等内容。
“无相”与“戒”之间留空,应该是为了象征该戒“无相”之特点。
法海--唐代僧人,曲江人,生卒年不详。根据《坛经》,法海是惠能十大弟子之首,他集录惠能在韶州大梵寺及平时说法而成《坛经》。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坛经》。
四、分段标点复议
敦煌本《坛经》首章包括标题、卷数、“兼授无相戒”、集记者等内容。这里主要讨论首章的书写格式,并由此探讨一些相关问题。
敦煌本《坛经》的首章是否有特定的书写格式?这是问题的前提。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仔细审核与比较敦博本、斯本、旅博本等三本的照片。所以要使用照片,是因为录文,包括本文的录文,受到条件的限制,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完全保留原件的格式。
上述三个敦煌写本中,敦博本的首章占两行: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
002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第一行顶天立地抄写,上部界栏并画有一莲花花苞状装饰。自“州”字换第二行,换行处文字意群割裂。这说明抄写者在抄写首章时完全没有考虑分行的问题。所以出现换行,是由于第一行抄不下那么多文字。
但敦博本首章也有自己的书写格式,它表现在:一、“无相”与“戒”之间有留空,约3~4个字。二、仔细审察可以发现,“戒弘法”三字,特别是“戒”字,比其余诸字略小。后来越写越大,乃至“法”字与“弟”字大小差不多。
斯本的首章占三行,形态如下: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003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第一行上端顶天,下端基本到行末,还留有约半字的空间;换行后第二行上端比第一行低一字。这说明抄写者是有意分行,不是因为第一行抄不下而不得不换行。换行处前后文字意群独立,标题被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也证明这是特意分行,不是被动换行。
第二行下端与第一行下端基本齐平,有约半字的空间;第三行上端低一字,与第二行齐平。在敦煌遗书中,这种抄写方式,意味着第三行与第二行本来应该是同一行,因为第二行已经到行末,下余的文字抄不下,只好换行,所以换行后的文字与第二行齐头。也就是说,“兼受无相”四字应上联。此外,“无相”与“戒”字之间也有留空,约2~3个字。“兼受无相”四字为细字。
根据上面的讨论,已完全可以证明敦煌本《坛经》的首章应有一定的书写格式。但这种格式到底怎样,还不是很清楚。但在旅博本中,敦煌本《坛经》首章的书写格式表现得最为清晰。
旅博本首章占三行: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
003┏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第一行上端顶天,下端在距离行末还有较大空间时,便特意分行。第二行上端不但比第一行低两字,并特意采用了一个在敦煌遗书中表示界隔的界隔符--“┏”【“┏”符,一般记于所标注字的右上方。本文限于条件,只能将它置于录文的上方。】。第一行所抄文字内容与斯本相同,意群完整。这说明在抄写者看来,自“六祖”起必须换行。
第二行下端尚有1~2个字的余空,第三行上端比第二行又低2~3字,并且也加上界隔符“┏”。这里是否表示“无相”与“戒”之间也一定要分行呢?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从斯本看,“无相”与“戒”之间显然不应该分行。那么,这里的界隔符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是提示在“无相”与“戒”之间必须留空。
仔细考察旅博本照片,第二行末尾“无相”两字的下面,虽然还有余空,但距离下边框线只有1~2个字的余地。而“无相”与“戒”之间至少需要空2~3个字,第二行末尾所留的余空显然不够。即使将第二行末尾的空白勉强当作留空,则“戒”字也必须分行另起,且要与第二行齐头。这样,如果读者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忽略第二行下面的留空。为了强调留空的必要,提示读者注意,抄写者特意弃第二行下面的余空不顾,“戒”字另起行后再留2~3字之空,并特意在“戒”字上标注界隔符。也就是说,旅博本证明,“无相”与“戒”之间,必须留空。
按照古代典籍乃至敦煌遗书的一般写法,作者与文献的标题可以分行书写,也可以合写成一行。没有一定的规范。如果不分行,则标题与作者之间一般应该留空。如伯3723号为《记室备要》,标题、作者作:
记室备要一部并序计二百八十七首乡贡进士郁知言撰
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与标题不分行,且与标题连写,不留空。但仔细观察旅博本可知,“兼受无相 戒”五字略小,“戒”字位置略偏右,反映出它与下文的“弘法”云云不是一个意群。也就是说,旅博本实际用细字及“戒”字的位置表示了《坛经》标题与集记者的区别。
综上所述,敦煌本《坛经》的首章的书写格式如下:
一、分行:标题本身应分作两行,自“六祖”以下另起,并低一格。“兼受无相戒”应上挂,与标题为一个整体。
虽然现存诸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均与标题连写,但从旅博本可知,集记者本身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意群。
二、留空:“无相”与“戒”之间要留空,作“无相戒”。约空2~3个字左右。
三、细字:从斯本“兼受无相”四字为细字,敦博本“戒弘法”字为细字,旅博本“兼受无相戒”五字均为细字分析,应以旅博本的写法为正确,“兼受无相戒”为细字。
“弘法”两字是否也为细字,需要研究。我的看法,“弘法”两字不是细字,这有斯本、旅博本为证。敦博本将“弘法”写为细字,恐怕是受直前“戒”字的影响所致。所以“戒弘法”三字,越写越大。
下面考察诸录校本如何处理《坛经》的首章。
一、郭本
由于郭本当时无条件参校敦博本、旅博本,故只根据斯本录文。郭本这样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
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郭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
第一、斯本标题分两行,郭本将标题合为一行(一个意群)。由于标题冗长,一行抄写不下,只好换行,成为二行。
第二、郭本将“兼受无相戒”五字下联,与集记者成为一个整体,并单独分行。
(二)留空与细字:郭本忽略了留空与细字,未予反映。
应该说,郭本对首章的书写格式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
二、周本
周本把《坛经》首章录校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慧)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
[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周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周本把首章分为三行。标题为两行,自“六祖”起分行,并低一格书写。集记者为一行。
(二)留空:周本认为留空乃是省略之意,故将原文的“兼受无相戒”补校成“兼受(授)无相戒受无相戒”,并进而将它们分为两段:前五字上挂,校“受”为“授”;后四字下联,“受”字不变。由此解决普授与特受的矛盾。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此处从略。
(三)细字:书写时将“[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周本注意到《坛经》首章书写格式的三个方面要求。但补校留空的方法值得研究。处理细字的方法也与原文不符。
三、邓荣本
邓荣本完全依据敦博本行款录文,从录文看不出录校者对首章的处理意见。但录校者将意见放在校记中处理:
我们认为:底本第一、二行中,“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是《坛经》正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是其副题,“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编者题名。有题名的三个写本中,以丙本(指旅博本--方按)书写形式最接近原貌,仅“戒”字当上属而误为下属【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18页。】。
但邓荣本的录校者之一邓文宽先生对敦煌本《坛经》的标题曾有专门的讨论,他在比较了三个敦煌本《坛经》的首章之后。指出:
上述《坛经》的三个标题,英藏本同旅博本比较接近,而敦博本却是另一番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旅博本第二行首字“六”比第一行低二字格,第三行首字“戒”又比第二行低二字格,且“六”、“戒”二字上均加有界隔号,用于避免混读。这说明《坛经》原标题共分三层含义:(一)其正题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副题是“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三)“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整理者署名。唯一的错误是,“戒”字本该属上文,英藏本和旅博本均误属在下文【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214页。】。
所以,邓文宽先生在自己整理录校的邓本中,用现代标点符号对《坛经》的首章作了如下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邓本的特点如下:
(一)分行:将首章按照正题、副题与编者分成了三行。分行时将“兼受无相戒”上挂。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邓本是唯一曾对《坛经》标题仔细研究的整理者。邓本的分行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坛经》标题的“正题”、“副题”之别,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邓本忽略了留空,且细字处理不当。另外,邓文宽先生认为旅博本将“戒”字误属下文,其实,如前所述,旅博本已经用细字及“戒”字的位置表示了“戒”字不应下属。
四、李本
李本对首章处理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李本的特点如下:
(一)分行:其分行方式也遵循主题、副题、集记者的思路,分作三行。但将“兼受无相戒”下联。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
由此,李本在分行、留空、细字等三个方面都有可斟酌处。
五、杨本
杨本对首章这样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
慧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杨本的特点是:
(一)分行:没有吸收新的校勘成果,分行完全依照郭本。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细字:将“一卷”处理为细字,又将“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全部写作细字,但比“一卷”两字的字号略大。
由此,杨本在分行、留空、细字等三个方面也都有可斟酌处。
六、潘本
潘本将首章录校如下: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授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潘本的处理方式比较奇特。
(一)分行:
粗粗看来,潘校本录为三行,三行下端均有余空,没有出现自然回行,似乎说明潘本主张应将首章分为三行。但第二行与第一行齐头,第三行却比第二行低一格。又似乎说明潘本主张将首章分为两行,即从“南宗”到“一卷”为一行,下余为一行。
潘本没有正面说明首章到底应该怎样分。笔者推测,有可能潘本1995年初版时,已主张首章分三行。只是忽略了副题应该低一格书写这一敦煌本《坛经》特有的格式。
与分行相关的是对“兼受无相戒”的处理。潘本对此校记如下:
伦敦本“兼受无相”顶格(原文降一字,并非顶格,潘本此处有误。──方按),空二格书戒字。敦博本“兼受无相”下亦空二格书戒字。案“戒”字当与上“无相”连属,与“弘法弟子”分开【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及附册》,佛陀教育基金会,2001年,47页。】。
潘本在上文中主张“兼受无相戒”不应下联。那么是否应该上挂呢?潘本未置一词。在上述录文中,潘本将这几个字另起一行,低一格书写,则显然主张也不应上挂。如此既不下联,也不上挂,则这几个字岂不悬浮起来?潘本录文正是这样处理的,可参见上述潘本首章录校文。但潘本对“兼受无相戒”又有这样的校记:“敦煌俗写受、授不分,受当改授。”【同上。】既然改为“兼授无相戒”,则如上文所分析,应属普授,那就应该上挂。潘本既主张普授,又不愿上挂,宁肯将这几个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悬浮,还不说明理由,的确有点奇特。
(二)留空:忽略了留空。
(三)忽略了细字。
看来潘本对首章格式缺乏足够的研究。
综上所述,六个录校本对首章的处理各有千秋,相互之间没有完全相同的。加上笔者的录校,共有七种方案。意见歧杂的关键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章到底分不分行?分几行?怎样分行?其中涉及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兼受无相戒”?
第二,如何理解与处理“兼受无相戒”之间的留空?
第三,如何理解与处理细字?
下面谈谈我的意见。
第一,关于分行。
首章包括标题、卷数、“兼”文、集记者等四个内容。在此依次考察分行问题。
首先,标题部分,亦即“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否应该分行?
如前所述,虽然敦博本对此不分,但斯本、旅博本均分,旅博本还特意作了分隔记号。由此,周本、邓本、李本、潘本的分行是正确的,而郭本、杨本的不分行是不对的。
关于标题问题,本文的“疏释”部分还要讨论,此处从略。
其次,卷数部分。
卷数应该连属在标题之后,这一点无论是敦煌遗书原卷,还是诸录校者的录文都是一致的,可以不再讨论。
再次,“兼”文,亦即“兼受无相戒”部分。
如上文已经分析的,“兼受无相戒”五字如果上挂,则“受”应校改为“授”,表示惠能向与会的所有成员传授无相戒,表示《坛经》中有授无相戒的内容。而这五个字如果下联,则应保留“受”字,表示法海是一个曾经接受过无相戒的僧人。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辨的重要问题。
诸多录校本中,意见极其分歧。郭本、李本、杨本主张不校改而下联,邓本主张校改而上挂,周本补校后既上挂又下联,潘本校改后既不上挂又不下联。但从敦煌遗书看,虽然敦博本、斯本都是既上挂、又下联,但最讲究首章的格式的旅博本却仅上挂,不下联。所以,我认为以旅博本为依据的邓本对此的处理是正确的,其余诸录校本的处理是错误的。
我们先看看主张下联的先生的意见。
李本、杨本主张下联,但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理由。郭本则申诉了理由。
有人将“兼受无相戒”连上,即《……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笔者以为,这有些牵强。因为,书题至《施法坛经》(特别是还有“一卷”二字),已经完结。如再连上“兼授”,不仅逻辑上难以说通,而且慧能“兼授”的,并不只是“无相戒”,光提一种,也很不完全。
……
“兼受无相戒”云者,法海身为比丘,必当已受比丘戒,从慧能学禅,复受“无相戒”,故称“兼受”【郭朋:《坛经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59页。】。
我认为上述说法值得商榷。
郭本主张“兼受无相戒”下联的理由之一,是标题到“一卷”已经结束。在“一卷”后附加内容,“有些牵强”。
在一般情况下,标题到“一卷”的确已经结束。但正如上文所述,敦煌遗书在用标题表述文献中的主要内容外,往往将其他一些内容,用细字标注于标题下。如前引伯3723号《记室备要》,它的标题“记室备要一部”之下有细字“并序”。这个细字就是补充说明标题的。在这里,细字作为标题的附属,与标题已经成为一个整体。郭本忽略了“兼受无相戒”这几个字也用细字书写,从而忽略了它们的附属标题的地位。
郭本的理由之二,是标题连上“兼授”,逻辑上难以说通,因为慧能“兼授”的,并不只是“无相戒”。
就《坛经》而言,惠能此次在大梵寺讲堂所说,可分为不请自说与应机而说两部分。其不请自说的部分,主要有三方面内容:述得法因缘、说法、授戒。述得法因缘,是为了宣示自己说法的合法性。下余的活动,只有说法、授戒两项。所以《坛经》开宗明义:“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由此,郭本的上述说法站不住脚。在这次法会中,惠能除了说法,兼授的只有“授无相戒”一种。
郭本的理由之三,是法海身为比丘,必当已受比丘戒,从慧能学禅,复受“无相戒”,故称“兼受”,所以应该下联。
如前所述,如果将“兼受无相戒”上挂,是指惠能对参加法会的信众普授无相戒。如果是下联,则是法海特受惠能授予的无相戒。如果的确是后者,而法海又特意将“兼受无相戒”标着在自己的名字上,则在当时,这种无相戒必然是非同一般的,只有具有特别根机或机缘的人才能得受,所以法海要把无相戒作为一种资格特别提出,冠在自己的名称上。但实际上,我们从《坛经》可以知道,无相戒乃是惠能普授给所有的信众的。既然无相戒像具足戒一样,是一种普授的戒,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那么法海有什么必要以此自炫呢?
“兼受无相戒”五个字既然不应该下联,自然只能上挂。
我们再看看周本的主张既上挂、又下联的意见。
周本主张“兼受无相戒”五字中的留空乃是省略,由此主张把留空补足后,校改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九字。前五个字上挂,后四个字下联。周本的留空乃是省略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一点下文再谈),所以则既上挂又下联的方案也不能说服人。
潘本既不上挂,又不下联的悬浮方案则更加没有道理。这种方案倒是符合数学的排列组合推演法,但无法从逻辑上得到论证。
最后,集记者部分。
敦煌本《坛经》的集记者部分均与“兼”文连写。但从旅博本可以看出,它与“兼”文实际是两个意群。诸种录校本均将集记者单独作一行。这种方法既不违反敦煌遗书的一般抄写格式,也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自然是可以依从的。
第二,关于留空。
诸种敦煌本《坛经》首章的“兼受无相戒”中均有留空。但六种录校本中,只有周本注意并力图解决这一问题。其他五种录校本均没有予以涉及。
周本这样说:
根据邓文宽君研究,敦煌写本,一般习惯,对于熟悉用字、用词,乃至短句,常采用空格形式,省去重复之字。所见极是。此处空格,即依其式样,补校“戒受无相”四字【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110页。】。
从而将“兼受无相戒”校补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九字,前五个字上挂,后四个字下联,企图由此解决普授与特受的矛盾。周本的上述方法不能成立。
在此,先看看邓文宽先生关于“空字省书”的论述。邓先生提出:“为了节省书写时间,古人除用省代符号代替某些字句之外,另一种方法是用空几字即不书字而省略。”【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209页。】并举出敦博本《坛经》中的一个例子:
《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认为“佛道”与“即时”之间的约两个字的留空,实际表示此处省略了“《维摩经》云”四字。由于敦煌本《坛经》的另一处还引用了“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八个字,前面的确注明“《维摩经》云”,所以,邓文宽先生的上述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是,敦博本《坛经》文中留空甚多,大抵表示句读段落。前引文字虽有约两个字的留空,如果把这留空看作是句读,文气亦连贯可通。而所谓“空字省书”,除了上述《坛经》中的一例,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其他用例。因此,这种“空字省书”是否可以作为敦煌遗书的书写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即使邓文宽先生上述“空文省书”的书写规则可以成立,这种规则能否同样套用于标题的书写,还是一个问题。起码邓文宽先生自己没有在邓本的录校中套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坛经》标题中的“兼受无相戒”的留空问题。
按照邓文宽所说“空文省书”的方式,所省应该是熟语。而周本所补的“戒受无相”,显然不能归为熟语。此外,将“兼受无相戒”校补为“兼授无相戒受无相戒”,行文累赘罗嗦,与《坛经》的风格完全不合。还有,如前所述,既然无相戒属于普授大众的戒律,则法海实在不必专门将它揭示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所以,周本把“兼受无相戒”的留空作为省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那么,这一留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可能是抄写者为了强调无相戒“无相”的特点,特意留下的象征性的表象。当然,虽然后代禅宗确有采用象征性表象的做法,但此处的留空是否也属此类,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关于细字。
敦煌本《坛经》首章有细字。但仅局限在“兼受无相戒”五个字。这五个字所以写作细字,是为了体现它附着于“一卷”之后的地位,以及表示该文献还包括授无相戒。诸录校本中,郭本、潘本完全忽略了细字问题。周本、邓本、李本、杨本看来有细字,但其瞩目点是集记者。将集记者写作细字,包括杨本将“一卷”写作细字,实际是现代人的书写习惯。这种方法虽然不违反古代文献的书写习惯,但与敦煌本《坛经》原有细字的意义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的录校本,应该保持原本固有的研究信息,不使流失。
综上所述,我认为敦煌本《坛经》首章的正确书写法应该是: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五、疏义
这里想谈谈敦煌本《坛经》标题及其相关问题。
我曾经撰文这样说:
邓文宽先生提出敦煌本《坛经》的标题实际由正题、副题两部分组成。站在上述考察的立场上,我认为这个观点基本上可以成立。有意思的是,据我的印象,中国古代书籍似乎没有正题、副题之分,这种取名方法是近代西学东渐以后才有的。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则正题、副题的取名法,在古代已经出现了。--哪怕只是一个特例也罢。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敦煌本《坛经》的副题与它的原题最接近,而它的正题是后来产生的。我认为很可能是神会滑台大会与北宗争正统以后出现的。这与敦煌本《坛经》本属神会系传本也正相吻合【方广锠:《谈敦煌本〈坛经〉标题的格式》,载《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144页。】。
我的基本观点在上文已经表明,即:第一、敦煌本《坛经》的副题产生在前,与原题最接近;而正题产生在滑台大会之后。第二、敦煌本《坛经》是神会系的传本。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下面简单谈谈。
敦煌本《坛经》的标题甚为冗长,这样风格的标题,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少见到。主要因为它由正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与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两个部分组成。那么,《坛经》最早的标题是否就是像敦煌本这样,有两个部分呢?
现知的《坛经》传世本,除敦煌本外,有惠昕本系统、契嵩本系统的传本存世。惠昕本是惠昕于北宋乾德五年(967)改编的本子,它当初的标题是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属于惠昕本系统的日本京都兴圣寺本的标题作“六祖坛经”;也属于惠昕本的日本石川县大乘寺本及金山天宁寺本的标题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由契嵩于至和三年(1056)改编的契嵩本系统标题基本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些标题都比较朴实,大体相当于敦煌本的副题。但这些本子出现得比较晚。在唐代,《坛经》是否还有别的名称呢?
日本入唐僧圆仁(794~864)撰于承和十四年(847)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了一部《坛经》,作:
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一卷,门人法海译【《大正藏》卷五五,1083b。集记者原作“沙门入法译”,据校记改。】。
据说,诔?使趴?局幸灿械米蕴拼?摹短尘?罚?晏庥朐踩时鞠嘟??鳎?br>
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释沙门法海集【参杨曾文:《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234页。】。
上述标题与敦煌本的正题、副题都不一样。但比较而言,上述标题的前半部分与副题的前半部分有所相同。
日本入唐僧圆珍(814~891)于大中八年(854)所记《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也载有《坛经》一部,作:
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一卷,门人法海集【《大正藏》卷五五,1095a。】。
在圆珍大中十一年(857)所撰《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中,以及大中十二年(858)所撰《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再次著录了这部《坛经》:
曹溪能大师坛经,一卷【《大正藏》卷五五,1100c。《大正藏》卷五五,1106b。其中《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将“坛经”写作“檀经”。】。
圆珍著录的这两个名称,与敦煌本的副题比较接近。圆珍在两个不同的目录中,对同一部经典,著录了两个不同的名称。这或者可以用一繁一简来解释,但也说明当时对《坛经》的称呼还有一定的随意性。
上面几条都是唐代的资料。撰写于日本宽治八年(1094),相当于中国北宋绍圣元年的《东域传灯目录》对《坛经》的著录,就变成:
六祖坛经,二卷【《大正藏》卷五五,1164c。】。
这与契嵩本以及我国北宋起开始流通“六祖坛经”这一名称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资料,我认为,与诸多其他标题相比,敦煌本《坛经》的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就其形态而言,最为质朴。这个标题,即使不是《坛经》最早的标题,也与最早的标题最为接近。
惠能逝世后,神会主张以《坛经》传宗,携带着《坛经》北上。滑台大会上,神会指斥神秀系“师承是旁,法门是渐”,标榜自己的南宗才是正统,顿教才是无上法门,所以为《坛经》另立标题,也就是敦煌本《坛经》的正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标题是在激烈的论辩中产生的,因此有“最上大乘”之类充满战斗性的风格。神会系的禅宗后来传到敦煌,神会系的《坛经》也传到敦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
神会只是惠能的弟子之一。惠能的其他弟子也依据《坛经》传播惠能的思想。圆珍著录的《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曹溪能大师坛经》这两个名称,显然是从“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这类名称中化出。后代惠昕本的“六祖坛经”、“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契嵩本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都是从这一名称转化来的。
圆仁著录的“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檀经”与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一批禅宗南宗文献的标题风格一致,可见是在南宗席卷中华大地时,有人仿照南宗文献的风格改编的。它与敦煌本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应该是惠能其他弟子所依据的传本。
也就是说,通过对《坛经》标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敦煌本《坛经》并非最早的《坛经》传本,而只是神会系的传本。当时,与神会系《坛经》同时流传的,还有其他一些《坛经》传本。这或者能够解释后代《坛经》歧杂多样的原因。
我国胡适曾经提出,敦煌本《坛经》是神会编纂的。他的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赞同。但是,胡适的确发现了敦煌本《坛经》与神会系具有的密切关系。在敦煌本《坛经》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内证,证明该本曾经神会系僧人的改纂。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进行过论述,本文在此从略。本文对敦煌本《坛经》标题的研究,也证明该本确为神会系的传本。
六、原始资料
下面将诸种敦煌本《坛经》的首章录文如下,以为参照。
敦博本: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
002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斯本: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003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旅博本:
00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002┏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
003┏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方广锠,1948年生,江苏邗江人。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系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院佛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河北禅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发表有《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印度禅》、《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合著)等专著。)

峨山慈棹禅师在月船禅慧禅师处得到印可,月船就对他说道:“你是大器,至今终能成就,从今以后,天下人莫能奈你何,你应发心再参善知识,不要忘记行脚云游是禅者的任务。”有一年,峨山听说白隐禅师在江户的地方开讲《碧岩录》,便到江户参访白隐禅师,并呈上自己的见解,谁知白隐禅师却说道:“你从恶知识处得来的见解,许多臭气薰我!”

五十五卷。明·憨山德清撰,侍者福善录,通炯编辑,刘起相重校。又称《憨山老人梦游集》。为憨山德清语录的集大成本。收在《禅宗全书》第五十一册、《万续藏》第一二七册。作者德清,晚年号憨山老人。与云栖盐宏、紫柏真可、蜀益智旭等三人被称为明季四大师。治学范围极广博。除佛教经论之注疏外,另有关于《老子》、《庄子》、《中庸》等书之注解。

迦叶二十八传至达摩,达摩五传至曹溪六祖六祖后派列五家。六祖传青原思祖,思传南岳石头迁祖,迁传药山俨祖,俨传云岩晟祖,晟传洞山良价禅师,价传曹山本寂禅师,后人尊为曹洞宗。又石头传天皇悟祖,悟传龙潭信祖,信传德山鉴祖,鉴传雪峰存祖,存传云门文偃禅师,曰云门宗。

禅宗经典有哪些?《大般若经》是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临济宗为禅宗南宗五家之一,由希运禅师住持宜丰黄檗寺时暂露端倪。从曹溪的六祖惠能,历南岳、马祖、百丈、黄檗,一直到临济的义玄,于临济禅院举扬一家,后世称为临济宗。义玄是惠能的六世法孙。又临济六世孙为石霜之圆禅师。圆禅师以后分杨岐派、黄龙派。

我国著名高僧虚云大师,是禅门巨匠,是禅宗史上极为罕见的大器之人,是我国佛教继惠能大师后又一位伟大的觉者。虚云大师生于1840年,示寂于1959年,世寿120岁,僧腊101年。虚云身受禅门五宗法脉,即:沩仰宗七世、法眼宗八世、云门宗十二世、临济宗四十三世、曹洞宗四十七世。虚云喜禅,他晚年对弟子说:“余于初出家后,自审根器,当从行门人,故习苦行,

释迦牟尼佛→初祖摩诃迦叶→二祖阿难尊者(中经二十八代至)→西天二十九祖东土初祖达摩大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南狱怀让禅师→马祖道一禅师→黄辟希运禅师→临济宗第一代临济义玄法师(中经四十二代至)→虚云古岩禅师→净慧本宗禅师→寂仁常毅禅师→四十六代义辉寂月

《指月录》三十二卷。又称《水月斋指月录》。明·瞿汝稷集。万历二十三年(1595)完成,三十年序刊。收在《万续藏》第一四三册。

茉莉花茶对于懂茶的人来说就没有什么保质不保质期了。 包装商品不标生产日期与保持期晃能上架销售的。但这并不适合茶叶类。可是没办法中国的食品法要求必须这么做。 茉莉花茶是用绿茶与茉莉花反复窨制

印顺大和尚,字源利,湖北襄阳人。2000年于深圳弘法寺礼本焕长老为师剃度,为临济宗第四十五代衣钵传人,次年依广东云门寺佛源长老圆具。印顺大和尚出生于湖北襄阳书香之第。父亲执教乡学,熟读经史,教书之余,兼习笔墨。六岁母亲去世,由继母扶养成人。印顺大和尚自幼聪慧,心慈悲怜,不忍杀掠,喜欢放生,虽然生活贫穷,但是志向很高,喜欢探究天下宇宙与人生问题。小学期间成绩优秀,考入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县城高中,勤奋学习,努力拼搏,最终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

当你已经通晓道理与修行的理路,也已经知道如何教化众生,亦即理、教都圆备了。此时,就可了解诸法与诸法之间的所有法相,其实是全归于平等的。

只要有正觉的心,本性自然而显露。只要我们有正觉的心,那一切妄念就像一灯能照千年暗一样,只要我们有正觉的心,所有的业障、往昔所造的种种恶业全部熄灭。

以拥有的欲求看待现前心所对应的是心外求解决苦的方法,借由对苦觉知而生的离苦心去透过佛法所对苦的诠释,同时也觉悟苦而真的求出离,却不是暂时或是只单单对外求解决。哪怕是对外求解决也是需要对以往心所依、行为所做思维和转变,更何况要真的离苦求解脱。

禅定,是一个很幽胜深远的法门。有实修经验的人,一定会知道,你修得越深,精神层面的感觉将越深邃,越难以言诠。这种精神层面的感觉,只能透过实修去取证,自然会了解深刻的禅定里面是什么样的世界。

自己要检视自己修禅定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利养。如果是,那就是地狱的心。什么是地狱心?当此生此世贪得无厌,下辈子就容易掉入地狱。如果为了利养而修禅定,这就叫发地狱心。可千千万万要避免啊!

衣食支分婚嫁毕,从今家事不相仍。夜眠身是投林鸟,朝饭心同乞食僧。清唳数声松下鹤①,寒光一点竹间灯。中宵入定跏趺坐②,女唤妻呼多不应。 白居易的晚年,是个虔诚的佛弟子。在他的诗集里,有《赠僧五首》之一说:“百千万劫菩提种,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将何报答佛恩深。慈悲不瞬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每岁八关蒙九授,般勤一戒重千金。”诗名《钵塔院如大师》,并有小序说:“师年八十三,登坛秉律凡六十年。每岁于师处授八关斋戒者九度。”表现了对于出家人的赞美和欣美。这回轮到他自己坐禅学佛了。

解脱之法的发现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住世是僧众。所以,佛教把这能让众生离苦得乐的佛、法、僧称之为三宝。佛陀在世,佛教以佛陀为中心,佛陀入灭后,佛教则以僧团为中心。皈依三宝是为了学习正法,正法又须僧团来作良导。

做什么事都要以大悲为体、菩提心为相、种种方便方法为用。若是以大悲心为体智慧必然会显发,悲智运用如何也是要以菩提心为相,这样在依法行事和发心做事的时候,就不会以顾及而最终是以自我的寻思为顾忌,这样就会视一切为恶为不如法就会远离大悲,就不会发菩提。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成就别人,因为我们明白一切众生无其自性,受被成就的也无自性,成就的方法也无自性,这样我们就不执着了,因为有执着就会有因自我估计寻思而出现的好坏,这些好坏用常规看上去很对,但是却远离了大悲,就不会和无尽功德相应。

人生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格信誉,他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当一个人具备了这种良好的品行时,他的生活很充实,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不知所措,更不会迷途无归。

修禅就要平实,老实修,老实参,老实做。不要以神通来眩人眼目。当然有的人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总是以神通为修法的目的,或者以神通为动力、目标,立这样的志而去修学佛法。这样修学佛法,这样去用功,往往会落入外道的修学当中。所以我们这里切记不要在修禅定中以神通为目的、动力。否则容易走到外道邪路上去。当然,因为根基所致,很多人平实不了,平平淡淡怎么可以呢?我修行就是要修出一点动静来,这个动静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动静就是你心里面的动静,还是要息止它。

严格来说,佛教的戒和律是有所不同的。“戒”主要是强调带有一种自觉的性质,信众出于自身的意愿,发誓发愿,愿意遵守的一些行为准则、道德规范,这个是“戒”。“律”强调了外在强制的性质,就是说你加入僧团、或者加入教团,或者你加入一个宗教组织,那么你就必须遵守某些规章制度,你才能是这个这个团体组织的成员,这些规章制度就是“律”,它带有一定的外在强制

据《杂宝藏经》记载,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是象王,有这样一个具有功德的故事。《佛说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跟弟子讲,在往昔劫的时候有一个象王具有功德。过去,在劫初或善劫的时候,动物都会说话,而且有很多的功德,不像现在的动物特别愚痴,象王具有很多的功德。

一家之主,要乐观面对生活,心甘情愿去为这个家付出。没有怨言,没有计较,不挑剔家人的不是。儿子不好是自己的命,儿媳妇不孝顺也是自己的命。你讲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其实都不对,你也不对,他们也不对。一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都没有理。

不必仰望别人,自己亦是风景。什么是嫉妒心?很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嫉妒心,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有嫉妒心。先来看一下佛给出的定义。嫉妒定义:在《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里面,佛说:“其嫉妒者。自求名利,不欲他有。于有之人,而生憎恚(恨),是为嫉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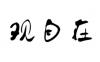
懂“观自在”者,是自己娱乐自己也。自己娱乐自己,就是自己去享受大自在、去享受稳定的情绪。去保持着不断提升的、源源不绝的生命动力,保持着美好的心情去帮助、去普度法界众生。凡人的情绪飘忽不定、难以自控,这是因为其不懂观自在。

我执重的人就是把自我的感受体现的越明显,他的我执就会越重。我执要靠什么来调伏,就是要靠理性、靠法,如果一个人靠感性那我执就会越重。假如说我们心里就是不舒服,但是用法来要求自己觉得自己不对,马上能调整,其实就是用法来破除我执。我们凡夫首先要破的是我执,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说要破自

在我们身边会发生很多事情,苦的、乐的、好的、坏的……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最后总会有一些转机,这个转机就是菩萨的加被、加持和关照。其实,菩萨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也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们。因为菩萨的大悲心使然,深妙微远、无有分别,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呵护。

今天是阿弥陀佛诞辰,阿弥陀佛成就的极乐世界是人类幸福美满的人生期盼和终极价值的最高追求。作为佛教徒,我们过阿弥陀佛诞辰,最重要的是系念阿弥陀佛,与佛道交感应。阿弥陀佛具备着无量的慈悲和智慧,我们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今天是冬月十七阿弥陀佛圣诞!阿弥陀佛是众生的慈父,西方极乐世界是众生的归宿!阿弥陀佛知众生苦,时时刻刻思念着我们!今天是他的生日,让我们通过几个小问题走进阿弥陀佛的世界,走进阿弥陀佛的怀抱!阿弥陀佛究竟是谁?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光佛、无量寿佛。

某僧刚出家时,早课、晚课、出坡、行堂、诵经、打坐等功课样样精进,而后慢慢心生懈怠,并不如前。某日,师上堂开示:无论出家在家,为什么有的人修着修着心态变了,问题出来了?你们可以扪心自问,当初修学的初发心是什么,坚持了多久,现在的心态又是什么?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