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镜与心鉴——宁波七塔寺开山祖师考
圣凯法师
关于宁波七塔寺开山祖师心镜禅师,七塔寺内现在仍然保存有心镜禅师舍利塔,塔高一公尺二十,塔座方形,高一公尺,上刻“唐勅赐心镜禅师真身舍利塔”十二字,上款“大清光绪丙午”,下款“住持慈云重修”其下碑文多漫漶不可读。民国陈寥士所撰《七塔寺志》的最后“补正”曾录文如下:
栖心寺
故禅大德藏奂和尚焚身五色
色舍利三千粒
时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进上七粒入内
道场廿九日唐勅赐谥号心镜大师
塔额寿相之塔勅奉为
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
皇帝延庆节建造此塔伏资
景福时咸通十四年岁次癸巳六月甲午朔
廿八日立知造石塔僧惠中
知造舍利殿僧[1]
从上面的铭文可以看出,此塔身为唐代所建。而且,“补正”又提到“《唐明州栖心寺藏奂和尚舍利塔碑》,刺史崔淇撰”,当时未能找到碑文,所以记载说“按此碑所述,必有大可记处,待考”。因此,有关藏奂和尚舍利塔碑,至少可能存在有两个。
有关藏奂和尚的传记,民国《七塔寺志》“补正”又依《宋高僧传》卷十二,补录《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2]清嘉庆重刊本《天童寺志》卷三,亦引用此传,并且加上“当师之天童也。在历游灵境,时逅会昌大中之际,其遗迹则徙清关之神龙于太白峰顶,镇毒蟒于小白岭上”的因缘,[3]说明藏奂和尚和天童寺的关系。后来,新修的《七塔寺志》则将藏奂和尚徙神龙、镇毒蛇的因缘补进进传记。[4]这些寺志所引用的原始资料都是来自《宋高僧传》卷十二“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另外,民国本《七塔寺志》记载藏奂和尚的师父为灵默,其谥号为“心鉴” (繁体字为“鑑”),而新修本《七塔寺志》记载其师为虚默,其谥号为“心镜”,旧新两种寺志,竟然有些差异,岂不怪哉?清嘉庆重刊本《天童寺志》、《新修天童寺志》则与新修本《七塔寺志》相同。[5]但是,《宋高僧传》记载藏奂和尚的谥号为“心鉴”,其师为五泄山“灵默”。[6]
总结上面的说法,有关藏奂和尚的师父和谥号,第一种说法:清嘉庆重刊本《天童寺志》、新修本《七塔寺志》、《新修天童寺志》的记载,其师为“虚默”,谥号为“心镜”;第一种说法:民国本《七塔寺志》、《宋高僧传》的记载,其师为“灵默”,谥号为“心鉴”。
我们查阅了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发现范氏于“心鉴”下有一注解:“按崔淇《心镜大师碑》,‘鉴\\\\\’作‘镜\\\\\’(《全唐文》卷八百四)。此盖宋人避庙讳(敬)嫌名而改,犹《龙龛手镜》之作《龙龛手鉴》也。”[7]按照范氏的提示,我们终于找到了崔淇所撰《心镜大师碑》,这无疑为七塔寺的开山祖师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根据《全唐文》所收《心镜大师碑》的记载,藏奂和尚的师父为“虚默”,其谥号为“心镜”,为第一种说法。[8]
另外,《嘉庆重修一统志·松江府志》记载:“藏奂,姓朱,华亭人。母生时,有异香。稍长,诣嵩岳受戒。大中间,居洛阳长寿寺。寻归姑苏,再住明州,所在学禅者云集。咸通中示寂,赐号‘心鉴\\\\\’。”[9]《松江府志》也是记载藏奂和尚的谥号为“心鉴”。
但是,我们对照《宋高僧传》“藏奂传”和《全唐文》的《心镜大师碑》,列表如下:
《宋高僧传》“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
《心镜大师碑》
释藏奂,俗姓朱氏,苏州华亭人也。母方娠及诞,常闻异香。为儿时尝堕井,有神人接持而出。
丱岁出家,礼道旷禅师。及弱冠,诣嵩岳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视,迨其归省,即日而明。母丧哀毁,庐墓间颇有征祥,孝感如是,由此显名。
寻游方访道,复诣五泄山遇灵默大师。一言辨析,旨趣符合,显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
会昌、大中,衰而复盛。惟奂居之,荧不能惑,焚不能热,溺不能濡者也。洎周洛再构长寿寺,敕度居焉。时内典焚毁,梵夹煨烬,手缉散落,实为大藏。
寻南海杨公收典姑苏,请奂归于故林,以建精舍。
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舍宅为院,迎奂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执兵昼入,奂瞑目宴坐,色且无挠。盗众皆悸慑,叩头谢道。寇平,州奏请改额为栖心寺,以旌奂之德焉。
凡一动止,禅者必集,环堂拥榻,堵立云会。奂学识泉涌,指鉴岐分。诘难排纵之众,攻坚索隐之,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
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现疾告终,享年七十七,僧腊五十七。预命香水剃发,谓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灭。门人号慕,乃权窆天童岩,已周三载。一日,异香凝空,远近郁烈。弟子相谓曰:昔师嘱累,令三载后当焚我身,今异香若此。乃发塔视之,俨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获舍利数千粒,其色红翠。
十三年,弟子戒休赍舍利,述行状,诣阙请谥。奉敕褒诔,易名曰心鉴,塔曰寿相。
奂在洛下长寿寺,谓众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昙粹是吾前生也,有坟塔存焉。相去辽远,人有疑者,及追验事实,皆如其言。初任生将迎奂,人或难之,对曰:治宅之始,有异僧令大其门,二十年之后,当有圣者居之。比奂至止,果二十年矣。
又奂将离姑苏,为徒众留拥,乃以椶拂与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焉?暨乎潜行,众方谕其深旨。又令寺之西北隅,可为五百墩以镇之。或曰:力何可致?奂曰:不然,作一墩植五株柏,可也。凡微言奥旨,皆此类也。刺史崔琪撰塔碑,金华县尉邵朗题额焉。
释氏之宗也,得了悟眞,机则旷劫不碍。自释迦去世,至曹渓已降,指心传心,祖系绵续,不分万派,不坠本枝。故得之者,则迥超觉路,坐越三界,大师之道契,万派之一流也。
大师讳藏奂,俗姓朱氏,苏州华亭人也。母方娠及诞,常闻异香,则知兜率降祥,来従百亿劫。糼怀贞悫,长契元奥。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淸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为儿时,常堕井,有神人接待而出。
丱岁出家,师亊道旷禅师。弱冠,诣中岳受具戒。母念其远,思之辄泣,因一目不视。及归省母,卽日而明。母丧哀毁,庐墓征瑞备显。由是名称翕然,归敬者众。因欲蕝茅诛木,与御燥湿。遽感财施充积,堂庑乃崇。院侧有湖,湖有妖神,渔人祷之,必丰其获。层量交翳,腥膻四起。大师诣其祠而戒之,鳞介遂绝。
后挈甁履,以厯湖山,灵境异迹。游覧将毕,复诣五泄山,遇虚黙大师,一言辩折,旨契符会。噫!显晦之道,日月之所照也。
圣教其能脱诸,故会昌、大中衰而复盛。惟大师居之,莹不能惑,所谓焚之不能热,溺之不濡者也。洎周洛再构长寿寺,敕度大师居焉。时内典焚毁,梵筴煨烬,手辑散落,实为大藏。
故南海节度杨公典姑苏日,请大师归于故林,以建精舍。
大中十二年,分寜任景求舍宅为禅院,迎大师居之。剡寇裘甫率徒二千,执兵昼入。大师冥心宴坐,神色无挠。盗众皆悸慑,叩礼逡巡而退。寇平,郡中奏请攺禅院为栖心寺,以旌大师之德。
凡一动止,禅者毕集,环堂拥塌,堵立云会。大师学识泉涌,指鍳岐分。诘难排疑之众,攻坚索隠之士,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
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现疾告终,享年七十七,僧臈五十七。先是命香水剃髪,谓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灭,门人童弟,号擗泣血,乃窆于天童巗。弟子培坟艺树,三载不闲。忽一日,异香凝空,远近郁烈,弟子相谓曰:昔奉大师遗嘱,令三载之后,当焚我身;今三载矣,异香其启我心乎!乃定厥议,揭龛发墖,再覩灵相,俨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礼法茶毗于天童巗下,祥风瑞云,竟日隠现。获舍利数千颗,红翆交辉,白光上贯。
十三年,弟子戒休赍舍利,述行状,诣阙请谥。奉勅褒诔,谥曰心镜,墖曰寿相。
鸣呼!菩萨之变通也。出显入幽,示现无极,其可究乎!大师自童孺距耆耋,陈言措行,皆贻感应。复以证前生行业,知示灭之日时。苟非位跻十地,根超十品,孰能造于是乎!
在长寿寺时,谓众僧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昙粹乃吾之前生,有坟墖存焉。相去辽远,人有疑者,及追验事实,皆如其言。景求将迓大师也,人或难之,对曰:治宅之始,有异僧令大其门;二十年之后,当有圣者居之。比大师至止二十一年矣!
初大师将离姑苏,为徒众留拥,乃以椶拂与之曰:吾弗在此矣,尔何疑焉!及大师濳行,众方谕其深意。又令寺之西北隅,可为五百墩以鎭之。众曰:力何可及?大师曰:不然,作一墩,种柏五株,卽五柏墩也。凡微言奥旨,皆此类也!至若辟元,关谕生死,宏敷至頣,不可备论。
咸通十五年,琪祇命四明郡,戒休以其迹征余之文,遂直书其事,以旌厥德。铭曰:
空王设谕,烦恼无涯,唯大师心,照尽尘沙。大师降灵,吴之华亭,方娠载诞,厥闻惟馨。童蒙堕井,神扶以寜,母思目眇,归省而明。渔人祷神,其获丰盈,一戒祠宇,施昄(?)莫婴。像敎中亏,贝叶斯隳,手集三乗,遗文可披。识羊祜环,知仲尼命,正色兵威,寄词谭柄。我来作牧,空企音尘,琢兹眞石,庻乎不泯!
《宋高僧传》“藏奂传》与《心镜大师碑》,其主要情节记载完全相同,文句也是相同。而且,赞宁提到崔淇所撰《心镜大师碑》,可知赞宁在撰述此传时,肯定见过此碑或碑文。可知“心镜”与“心鉴”定为一人。至于“虚默”与“灵默”,黄夏年先生《虚默·灵默·心镜——宁波七塔寺祖师刍议》则已考定为同一人,并且作出论证。[10]而且,“心镜”、“心鉴”既为一人,“虚默”、“灵默”则亦定为一人。
那么,“心镜”与“心鉴”这两个谥号中,哪个是原始的谥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龙龛手镜》又称为《龙龛手鉴》,范祥雍解释为避庙讳(敬)嫌名的缘故。但是,《龙龛手鉴》卷首智光“序”所引︰“以新音偏于龙龛,犹手持于鸾镜,形容斯鉴,妍丑是分,故目之曰《龙龛手鉴》。”[11]可知其题号由来。“镜”、“鉴”相通、混用、连用在古籍中非常普遍,“如镜鉴像而无心”[12]、“如百千明镜鉴像”[13]、“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鉴。若将镜鉴,便为两段”[14]。正是因为“镜”、“鉴”相通、混用,所以在避讳时,可以改“镜”为“鉴”。
《全唐文》所收崔淇撰《心镜大师碑》的发现,为我们考察七塔寺藏奂和尚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这样,藏奂和尚的师父为灵默(即虚默),其谥号为“心镜”(即心鉴)的千古疑案大概可以冰释了。
圣凯
2003年1月5日
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
[1] [民国]陈寥士撰《七塔寺志》补正,1937年排印本,《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1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影印,第235-236页。
[2] [民国]陈寥士撰《七塔寺志》补正,第238-240页。
[3] 清嘉庆重刊本《天童寺志》卷三,《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13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影印,第176页。
[4] 张秉全主编《七塔寺志》卷五,宁波七塔禅寺1994年出版,第71-72页。
[5] 天童寺志编纂委员会编《新修天童寺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34-135页。
[6] 《宋高僧传》卷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778页下-779页上。
[7] 《宋高僧传》卷十二,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第295页。
[8] 《全唐文》巻八百四,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3746页。
[9] 《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二千二百五十册,《松江府志》,《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10] 黄夏年《虚默·灵默·心镜——宁波七塔寺祖师刍议》,南华禅寺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禅学研讨会论文。
[11] 《新编龙龛手鉴序》,《四部丛刊·续编·经部》。
[12] 《宗镜录》卷六十五,《大正藏》第48卷,第780页上。
[13]《潭州沩山灵佑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卷,第580页中。
[14]《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卷四,《大正藏》第48卷,第178页中。

《安士全书》是“善世第一奇书”,超古超今,诚为传家至宝。全书共分四部,包括戒杀之书《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欲海回狂》;《阴骘文广义》;《西归直指》。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西归直指》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

每个人晚上睡觉时,从他躺在床上到真正睡着,中间起码有5到10分钟的时间。而对普通人来说,这几分钟,基本是在妄想与昏沉当中度过。这样带着妄想睡觉就容易做梦,引起睡眠质量越来越差。而学佛的人,懂得珍惜时间,把握当下。

弟子众等,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期生净土。又以业重福轻,障深慧浅,染心易炽,净德难成。今于佛前,翘勤五体,披沥一心,投诚忏悔:

我住在乌敏岛时,有一只狗跑到我那里去;而在戒律中出家人是不准养狗的,所以我也只是把一些吃剩的食物丢给它吃。有一次,我有事情要处理,于是把门锁上后就离开。隔天,当我把门打开时,它很快的从里面冲出来。我忽然间想起自己把它锁在屋内,之后四处查看,却发

一个人对事情不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嘴里不要乱说,肚子里明白就好。嘴巴叨叨不休,无事也会变成有事,最后总是会害到自己。那些没事叨叨的人切要注意,这样最会惹事。

佛教不是偶像崇拜者,如果要说佛教有崇拜的话,那么,他是崇拜智慧的宗教。在佛教初创期,佛教没有佛菩萨像,仅雕刻莲花、轮宝等作为佛法的象征。佛陀圆寂前曾经留言,我死之后要依法不依人,一切以佛法为最高。但是佛弟子们从内心尊重他的人格,

现在有的家庭不和,一天到晚总是吵架,就是因为过去生中造了太多恶口的业所招感的。对于恶语伤人这种恶业,有的人会拿直爽来做挡箭牌,还有的人会说自己刀子嘴豆腐心,说“我这个人就是心直口快,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借口。

吸烟,我们是不允许吸的,好像僧人戒律当中没有规定,但是有没有相应的呢,比如我们这种五辛,吃肉吃五辛,这些扰乱心性,断大悲种性,我们修学菩提道,这些都是根本。所以,菩萨戒里规定食肉、食五辛,都是不允许。辛辣的东西增长欲望,而且,吃了辛辣的东西,

世尊在《观经》第九观跟我们开示: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有八万四千好。讲“八万四千相好”,这是就大乘而言。讲“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形好”,这是就小乘而言。事实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佛为什么有如此的相好光明?这是“修因感果”,还是不离开“

这没有什么可疑惑的。睡和醒,这是我们妄念的产物,实际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白天的清醒仍然还是在梦中,所以白天和夜晚做梦,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但往往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第六意识处在一种休息状态,然而我们深层意识、独头意识还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如果透过念

杂念是病,佛号是药。我们无始劫来,被无数妄念所缠绕,不可能初始念佛便能将杂念剿灭,这得经过一个刻苦精修的过程,方能太平。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问:轮回是看不见的,应如何理解呢?济群法师答:轮回,其实是内心迷惑的显现,根源就在我们的心。换言之,在我们的凡夫心中具有六道众生的心理特质,当这些心理外化后,便呈现出流转轮回的种种状态

修习依止法,能为学人带来哪些殊胜利益呢?《道次第》总结为九点。1.得近佛位:如法依止善知识,能使我们迅速接近佛果。

现实中,不少佛子对“解脱”一词心存偏见,似乎这就是“自了”的代名词。当我们说到解脱时,许多人会觉得这个目标似有小乘之嫌。因为我们是以大乘自居,以菩萨学人自居,理应以利益一切众生为己任,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解脱。

佛,就是觉者,意味着生命的彻底觉醒。反过来说,众生就是迷者,是处在颠倒迷惑的状态。但我们不必气馁,因为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转迷成悟的方法。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每个众生都具有觉悟的潜质,具有自救的能力。

禅修所做的,就是帮助我们培养正念,把心带回到当下。这样,我们才能从情绪和妄想的缠缚中脱身而出。如何才能把心带回当下?佛教中,最基本的修行就是戒定慧,又称三无漏学,也就是三种导向智慧的途径。其中,又以戒为基础,所谓由戒生定,由定发慧。

佛法以缘起看世界。这就告诉我们,每种想法和情绪既非无中生有,亦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因缘和观念引导下形成的。错误的观念,正是负面情绪产生的土壤。

所谓无明,就是看不清自己的内心,看不清生命的真相,看不清那些此起彼伏的念头是什么时候生起,又是什么时候占据我们的心。

很多人都在说,今天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这种浮躁表现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当下的心理状态。

《楞严经》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谓一切圣贤,能转万物,不被万物所转,随心自在,处处真如。我辈凡夫,因为妄想所障,所以被万物所转,好似墙头上的草,东风吹来向西倒,西风吹来向东倒,自己不能做得主。

道究竟如何在行者当下去体证,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道不是一种客体,一种认知对象,而可以作理智测度。从禅宗来说,这种理智测度正是情识的分别作用,是无明烦恼的根本,必须勘破。

通常凡是有心或有兴趣于禅修的人,比较不容易有宗教层次的信仰心,因为信仰本身是属于感性,而禅修的人,多重视自己的修行,希望从修行中得到身心感应,得到禅修的经验,因此很不容易接受宗教层次的信仰,其实这是绝对错误的事。

井陉县信外道门的很多,我讲经的时候,他们的大老师,和弟子们都天天去听。有一天晚上,我和同住的房东先生闲谈,他也是一位外道的信徒,他说:

有人问:很多人认为,信仰只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归宿。若年轻时就信仰佛教,难免与生活和事业发生抵触。不妨等老了再考虑这个问题。

修每一法时,我们都要观察并思惟,这么修有哪些殊胜利益,不这么修有哪些过患。这很符合凡夫的心理,是人之常情。修布施也是同样,首先要思考执著色身、财富等有哪些过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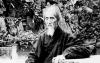
昔日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还可趣向也无?”泉曰:“拟向即乖!”州曰:“不拟争知是道?”泉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也那!”州于言下悟理。

凡夫通常处于无明状态,迷失真性,追逐妄心,随妄心流转,不知舍妄归真。所以,我们还要修行。

问:弟子总是过分在意别人的感受,深怕自己说的话或者做的事伤害到别人,弄得自己经常担心来担心去的,怎么办?

夫诸法实相,本自如如,无无明,亦无非无明,无法性,亦无非法性,奚必待破而始见?乃众生拘于习气,妄自思议,而初研教理者,又非如是不足以开悟,故随宜而申其说。

如来出世,唯一大事因缘,要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祖之道,原无二致;度生方便,乃有多门。诸佛以随机施化,四悉利生,一代时教,无非应病与药,原无实法与人。祖师棒喝,亦是一期方便,为人抽钉拔锲,解粘去缚而已,皆破执之具也
赞助、流通、见闻、随喜者、及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依佛菩萨威德力、弘法功德力,普愿消除一切罪障,福慧具足,常得安乐,无绪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生涅槃正路。家门清吉,身心安康,先亡祖妣,历劫怨亲,俱蒙佛慈,获本妙心。兵戈永息,礼让兴行,人民安乐,天下太平。四恩总报,三有齐资,今生来世脱离一切外道天魔之缠缚,生生世世永离恶道,离一切苦得究竟乐,得遇佛菩萨、正法、清净善知识,临终无一切障碍而往生有缘之佛净土,同证究竟圆满之佛果。
版权归原影音公司所有,若侵犯你的权益,请通知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